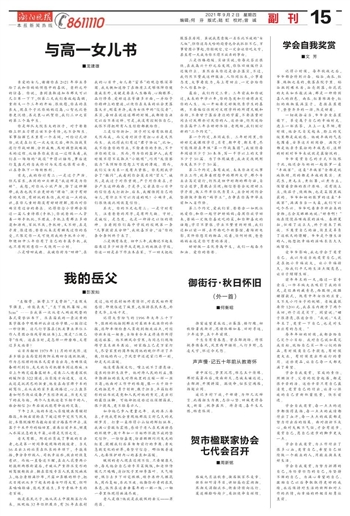■彭发灿
“左髂骨、耻骨上下支骨折”,“左髋关节强直,功能丧失”,“左下肢肌萎缩,短5cm”……当我第一次从老人码放规整的各式荣誉证书下,压在箱底的一叠泛黄的医学报告中艰难辨认出这些字眼,心脏掠过一秒惊颤。这几行字落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伤残等级证书》上,便是“二级乙等”伤残。这在当时,是怎样一种磨难,又有过多大痛苦?
让日历翻回1979年11月的旧光阴。道县乡镇企业局需到衡阳采购四台造纸机械,作为总经理的他本无需亲自出马,为确保设备顺利到位,先天就与司机驱车到达雁城。8日上午购完设备装好车,司乘二人迎着深秋的暖阳沿322国道,往零陵方向进发。这天我还是玩泥巴的孩童,他坐在南京牌卡车的副驾位,正从我的家乡泉湖路过,心上盘算着如何尽快让设备产生经济效益。历史天空下的我与他,两个人生轨迹毫不相干的人,谁会相信20年后彼此能有命运的交集。
下午2点,他的车进入零陵境画眉铺村路段,车辆右前轮在下坡过程中突然飞脱失控,车像脱缰野马般向右前方路基外冲去,滚落于十米开外的稻田里。若再往前半米,倾覆入水深流急的大干渠,必将是灭顶之灾。
老天有眼,附近社员成了事故的目击者,也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的救援者。当天56名出工的社员在队长的率领下,手撬肩抬,争分夺秒救人。司机幸运些,救出时恢复意识。而他一直昏迷不醒,在众人花费两小时撬断两根桁梁后,才被从严重挤压变形的副驾驶舱救出。躺在零陵专区人民医院病床上,他全身缠满纱布,只露口鼻眼的样子,把次日闻讯从乡下赶来的妻女吓得大哭。但听其喃喃轻语,能死里逃生,多亏素昧平生的老百姓。
他是农民之子,他从泥土中摸爬滚打而来。纵观他32年任职履历,有26年在农村度过,他对农村始终有情怀,对农民始终有感情。即便住进了城里,也保持农民本色,朴素无华,土味十足。
记得大雪纷飞的1996年大年三十下午,值班的他接到群众对某班车乱涨价的举报,迅即率领检查人员赶到相关站点,对经停班车逐一核查,当场责令车主将违价所得退还旅客。他不顾风冷雪寒,与同志们现场蹲守至末班车离站。回家路上已是万家灯火,尽管家里的团年饭因他的晚归早凉了半截,但他的内心,于风雪中迈进家门那一刻,却是无比温暖。
他没有高深文化,嘴上说不了漂亮话。漫长的任职生涯中,他对待人民的利益,像辛勤耕耘的农夫对待地里的庄稼一样一丝不苟;他面对工作中的难题,像一头干劲十足的拓荒牛,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半箱红彤彤的证书就是党和人民对他的肯定,是出彩的最佳注脚。可他却把这些过往深埋箱底,很少提及,更不轻易示人。
如今他已步入耄耋之年。我的再三要求,才使我有机会重现他那段尘封已久的光辉岁月。打量一桌堆得小山似的鲜红证书,我满心崇敬与震憾,感动于老人在充满诱惑的环境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怀抱不放的坚定信仰。一份份嘉奖,仿若颗颗闪闪发光的红星,提醒我们后辈匆匆前行的步履: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要坚守信念。哪怕做普通人,也要保护好内心的善良和温暖。
赋闲的老人现在还闲不住。只要健康允许,每天他会自己动手买菜做饭,和老伴侍候几只鸡鸭,清扫院子里四季落叶。天气晴好,偶尔去乡下旧宅瞧瞧,顺手再种几棵花木,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他勤俭朴素的农民本色,依然在这垂垂暮年的一粥一饭、一锄一帚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老人是谁?他就是我敬佩的岳父——蒋德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