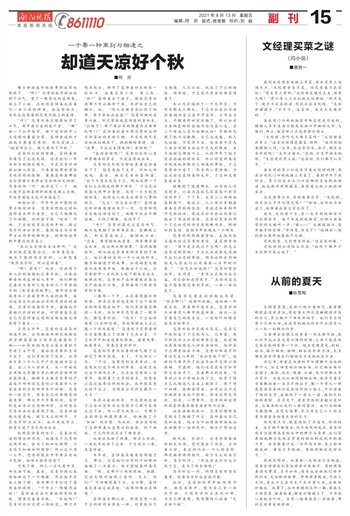■陈雪梅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妹打着哈欠、揉着眼睛跟在母亲身后,得趁着太阳还没睡醒稍凉快的当儿,拿上镰刀下田收割稻子。我们家当时有十几亩水田,在没有机械化的时代全得靠人工一粒一粒颗粒归仓。
父亲那会在镇上经营着一间豆腐作坊,农忙时节也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父亲只能在赶完集后赶回家帮一下忙。起五更摸星光,割稻、扮禾、踩打稻机、插秧、晒谷这些体力活,大多都是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没日没夜地在忙活。
记忆里,母亲是双抢时节忙得脚不沾地的那个人,忙完田里的忙晒谷场,忙完晒谷场忙菜园子,做饭、洗衣、喂猪、打柴,马不停蹄又井然有序。无数次从田间到晒谷场,母亲弓着背弯着腰担着一百多斤的谷子,像一个男人一样晃晃荡荡来回行走在坎坷的小路上,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背,盐碱结了一层又一层,扁担压红她的肩膀。在月光下,母亲黑瘦的身躯忙进忙出,总莫名的让我们心酸得落泪。我们五姐妹不敢偷懒,自觉又懂事,尽力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为母亲分担着生活的压力。
夜风有点凉,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特别的美。谷子晒干晒透后,风车迎风响起来,母亲用风车过滤掉混在稻谷中的稗子与杂质,我们需要踮起脚才能把笸箩里的稻谷倒进风车的漏斗里。母亲擦着汗说:“今年雨水好,垄上的田收成好。看谷子多饱满,有收有晒就是好日子。”
夜朗月明时,如果第一天的谷子没晒透,母亲会领着我们在谷堆旁守夜乘凉。有时候望着满天繁星,月华如水,母亲也会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天仙配的故事。即便浑身酸痛,可孩儿天性,竟也不忘在月光下去扑萤火虫,去捉纺织娘玩。玩累了,往竹席铺的禾坪一躺,数数天上的星星,数着数着,眼皮打架阖上了。不用担心被蚊虫叮咬,自有一把蒲扇在一旁摇着,那就是母亲爱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