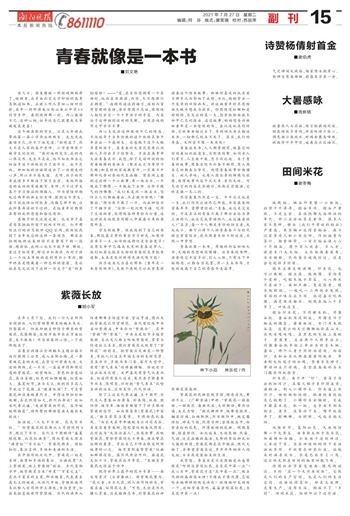■谢冬梅
收晚稻。晒谷坪里留一小块地,扫得干干净净,糯谷专用。糯谷产量低,不是主食。在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年代,种三五分地算是奢侈。很多人家不愿种,粳谷(我们平常说的稻谷)产量高,养家糊口还得靠稻谷。熬不过家里老人和小孩念叨,仔细掂量与算计,勒紧裤带,一百斤稻谷换七八十斤糯谷,图个家人欢喜。不入仓,请进专门大木柜。大木柜挨着屋角,安安静静,然而每当视线经过,还是会勾起许多停留。
糯米主要是做酒糟、炒米花,也可以熬粥、酿豆腐、做麻圆。家伯有个爱好,吃糯米饭不用菜,七八两米不在话下。若加点糖,更是佳肴。糯米饭软粘,一般吃一二两就会发腻,家伯的口味与众不同。他还喜欢吃麻圆,洒芝麻浇糖水。到现在他八十多岁了,口味没变。
糯谷炒米花,不用碾米机,用砻谷机。砻谷机用泥倒成,外围是竹子编成的圆筐,磨齿粗深,专门用来脱谷壳。没有云的天空慵懒地卧在山头,北风吱嘎吱嘎,在黑色的秃枝上荡秋千。堂屋里,左右两个人跨步站立,同握砻谷机手把上牵出来的长木柄。砻谷,两个人身子同时向前俯,向后仰,米和谷壳从两扇砻磨间溅出。吊垂肥大红冠子的公鸡,竖着长长脖子,带领四五只母鸡,在堂屋高高的石头门槛前伺机抢食。
炒米花,离不开“炒”。密筛子筛出的细河沙,在柴火锅子里炒得滚烫,滴桐油,倒入小罐珍米。珍米遇上热河沙,啪啦啪啦地跳,跳着跳着就把自己跳肥了。小罐珍米出锅时,变成半撮箕米花。抓一把,左手右手倒来倒去,烫手。没等冷下来,嘴早就张开了。肥嘟嘟,白胖胖,吃起来粘又细。
双抢时节,夏阳如炙,天地间仿佛一个大蒸笼。母亲取大杯子泡米花,加酒糟和白糖,打发孩子送到田边。父亲放下犁,坐在田埂的树阴下美滋滋地享用。牛就势在田里打滚,站起来时满身泥水,长尾巴后背上一甩,过往的光阴在时间的轴里四散飞溅。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说过,乡村“是一个天然共同体”,它既是人们的生产空间,也是人们的生活空间。这话说得直白,却是大道理。光有生产,没有生活,构成不了“乡村”。田间米花,恰好印证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