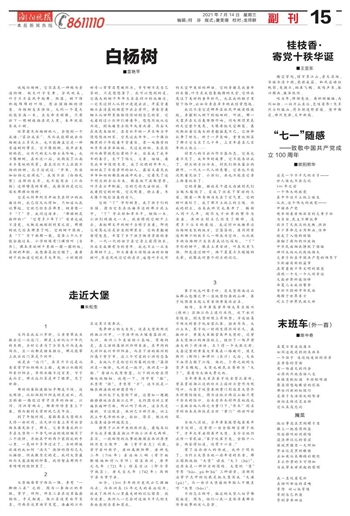■雷艳平
说起白杨树,它实在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树。秋天叶子变黄,金风吹来,叶子片片在风中起舞、飘落,树下堆积起绵绵的叶堆,有法国梧桐的诗意。白杨树生长很快,大约一个夏天就能长高一米,且生命力顽强,只要折下一根树枝插在泥土里,来年就能长成小树。
经常看见白杨树的人,会想到一个成语:“茁壮成长”。然而我能够说出白杨树这么多优点,也不能掩盖它是一种普通树的事实。它不像桃树,能开出美丽的花,让历代的文人雅士来吟咏;也不像柳树,在水边一站,就构筑了江南水乡柔婉的风景;甚至还比不上其貌不扬的柏树,孔子还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写不出《白杨礼赞》这样的文字,也不能写出《小白杨》这样嘹亮的军歌,我要写的是记忆深处那棵白杨树。
它是从何年何月开始长在村口的池塘边的,我已经无从得知。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它就已经长在那里,树身像一个“丫”字。我问过母亲:“那棵树是谁种的?”“它有多少年了?”母亲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她嫁到村里之前,那棵树就已经在那里了吧。它的树干很粗,在“丫”字下面那一截,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小学时候有门课程叫《自然》,课本里说树干里面一圈一圈的纹,是树的年轮。我想要是把它锯了,看看树干就知道它到底多大年纪。小时候的好奇心常常具有破坏力,幸亏树不是自己家的,只是想想罢了。我可以想到的是,它高大的树干年年生长在村口的池塘边,一定见过村人从村口进进出出,早晨背着锄头在清晨的朝霞中出去劳作,黄昏背着锄头从田野里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家。它也看到过小伙伴们骑着牛,悠悠然地从远而近,到池塘里去饮牛或者洗澡。然后又在夜色来临时,在老水牛的一声长哞当中慢悠悠地回家。它见过我爷爷,一个强壮黝黑的少年赶着牛背着犁,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养活弟弟妹妹。见过我奶奶,生在农村而面带桃色红晕的少女,后来成了我爷爷的妻子,生下了伯父、父亲、姑姑。看见我爷爷慢慢变老,成了沉稳的中年人,奶奶成了日夜劳作的妇人。最后又看见我爷爷和奶奶都在病痛中死去,它看见了这个村庄的古往今来。根在地下汲取营养,叶子在云中飘摇,它的悲伤无法诉说。等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沉默着、静立着,冬天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它的“丫”字形树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因为它长在池塘岸边的那方泥土中,“丫”字正好和岸齐平,相隔一米。小孩们稍微大一点,就会跨到它树干上去,再把那叉开的树干当椅子坐着,即使父母骂也还是会坐到那里去。它的身躯被磨得发亮,丰富了乡下孩子物质贫瘠的童年。一代一代的孩子在它身上获得快乐,然后变成强有力的青年。我也不止一次坐在那树干上,仰头看着头顶绿油油的白杨树叶,享受风吹过它的清凉,遥想叶子之外的天空中美丽的神话。它的身躯是我童年的乐园,叶子是我想象驰骋的天堂。它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也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烙印,让如今身在异乡的我经常想起。
我记不清它是哪年在狂风中被连根拔起,身躯倒入树下的稻田的。听说,那一天雷声在天边轰隆隆作响,闪电照得黑色的天空整个发亮,又像要把天空撕裂。暴风撕扯着它高大的身躯摇晃不已,它拼命抗争了好久,终于一声巨响,重重地倒在了那片它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土地上……
村里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再也看不见了。我爷爷的故事,它不能告诉我了。村庄的古往今来,村民们朝来暮去的耕作,一代又一代人的更替,它再也不能沉默着见证了。小孩们,再也不能在它身上爬着玩乐了。
它的身躯,据说是干透之后被村民们当做木柴烧了,变成了灶底下窜动的火苗,随着一阵青烟消失在了空气里。它的树叶腐烂了,成了那片土地上的尘埃。而我的村庄,后来我终究也离开了。辗转人间十几年,阅尽大千世界的繁华与沧桑,再回去村庄已经变了模样,没有多少往日的痕迹。走过村口池塘岸边白杨树生长的地方,空荡荡的,连同村里逐渐稀少的故乡人一样成为空白。从此故乡的白杨树只生长在我记忆深处,“丫”字形的树干,根在土里安详,叶在风里飞扬。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星星点点暖暖的光晕,就像我对整个村庄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