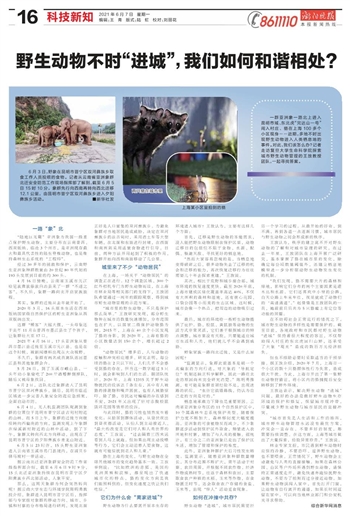上海某小区里拍到的貉
一群亚洲象一路北上进入昆明市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闯入村庄、貉在上海100多个小区现身……近期,多地不时出现野生动物进入人类栖息地的事件。对此,我们该怎么办?记者走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团队,一起寻找答案。
一路“象”北
“陆地巨无霸”亚洲象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临沧3个州市,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也是维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
经过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93头发展到目前的约300头。
4月16日傍晚,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不久后,象群一路向北开启家族旅程。
其实,象群的迁徙从去年就开始了。
2020年3月,16头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
这群“稀客”大摇大摆,一头母象还于去年11月在普洱市墨江县生了个孩子,让象群壮大至17口。
2021年4月16日,17头亚洲象从普洱市墨江县迁徙至玉溪市元江县。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新闻爆料出现在大众视野。
不久后,象群有两名成员离队返回墨江县和其他象群会合。
5月24日,到了玉溪市峨山县,一头年幼小象偷吃了200斤酒糟醉倒掉队,随后又被母象找回。
6月2日,这队北迁象群进入了昆明市晋宁区双河彝族乡。随后,昆明市临近区域进一步完善人象安全防范应急预案,全面启动布防。
6月4日,无人机监测团队观测到象群的位置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法古甸村附近的山林。而5日上午,象群的迁徙方向继续转向西偏南的方向,监测发现上午象群在绿溪新村附近的山林中活动。到了下午,象群又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出现在了昆明市晋宁区的夕阳彝族乡青龙山附近。
6月5日23时许,15头野生亚洲象进入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境内,在浦贝乡驿马坡村一带活动。
据云南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介绍,截至6月6日9时9分,15头北迁亚洲象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西北部活动,人象平安。
那么,这两天象群为何会突然转向呢?据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陈明勇教授介绍,象群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后,指挥部与专家组对象群的移动方向、城市、乡镇和村寨的分布格局进行研判,发现北面正好是人口密集的双河彝族乡。为避免象群对当地居民造成威胁,决定在双河彝族乡的法古甸村,釆用渣土车等大型车辆,在北面和东面进行封堵,在西面和南面则采用适量食物进行引导。目前,两种方法并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象群开始向西和南面移动了几公里。
城里来了不少“动物居民”
在上海,一场关于“动物居民”的调查正在进行。12个调查区域、300个红外相机专门为野生动物而设,在上海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王放团队希望通过一两年的跟踪观察,得到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示范方案。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不只是保护那么简单。”王放研究发现,部分野生物种在城市的数量快速增加,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貉为例,2015年,上海在40余个小区发现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量达到150余个,增长超过2倍。
“动物居民”增多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和冲突相应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顷的貉在2只以下时,人们几乎不会感受到貉的存在,但当这一数字超过5只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据团队统计,2020年,上海12315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投诉达千条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噪声困扰,也有人被貉惊吓。除了貉,市民还对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现了针对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等情形的投诉。
与此同时,貉的习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独居到群体活动,从昼伏夜出到昼夜都活动,从怕人到主动接近人。“最大的改变是它们对人和人类世界的态度。”王放说,“过去隔着三四米远看到人马上就跑,但如果出现主动投喂等行为,它们会主动追着人要食物,这就有可能惊扰到老人和儿童。”
貉在上海的变化,与野生动物在全球其他城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王放举例说:“比如欧洲的赤狐、美国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现出了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貉的变化方向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但变化速度之快让我们吃惊。”
它们为什么会“离家进城”?
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离开原本生存的环境进入城市?王放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迁移是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没人能把野生动物限制在保护区里,动物迁移目的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敌、寻找更好的栖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当栖息地变得破碎之后,很多动物失去了迁移的机会和迁移的能力,再次恢复迁移行为往往需要几十年去探索重建。”王放说。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的恢复速度更快。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仅有大面积的森林和湿地,还有街心花园、口袋公园等小而美的生态区域。这时候,城市会像一个热点,把周边的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城市的环境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貉、松鼠、黄鼠狼等动物的生活方式非常灵活,它们善于根据城市的特点调整,城市里没有天敌,只要能适应城市生活和人类,他们就几乎不会遇到威胁。
野象家族一路向北迁徙,又是什么原因呢?
“监测显示,象群此前基本是朝一个北偏东的方向行进,对大象的‘导航定位’机制还缺乏科学解释,因此一路往北走的原因尚未完全研究清楚。”陈明勇推测,有可能是象群首领经验不足,出现迷路的状况。“也许它搞错路线,仍认为自己走的方向是对的。”
栖息地承载力下降也是重要原因。云南省亚洲象分布区的11个自然保护区中,10个属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类型。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森林郁闭度大幅度提高,亚洲象的可食植物反而减少,不少象群逐步活动到保护区外取食,频繁进入农田地和村寨,增加了与人类的接触。据统计,有三分之二的亚洲象已走出了保护区生活,增加了管理和保护的难度。
此外,亚洲象种群扩大后习性发生转变。监测显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常年活动于村寨、农田周围,并根据不同农作物、经济作物成熟时节,往返于森林和农田,主要取食农户种植的水稻、玉米等作物,在食物匮乏时节,还会取食农户存储的食盐、玉米等,出现“伴人”活动觅食现象。
如何在冲撞中共存?
野生动物“进城”,城市居民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好奇,到不满,再到各退一点逐渐习惯,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会形成新的秩序。
王放认为,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对野生动物的了解和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在过去一年里,王放团队在上海开展广泛研究,基本掌握了貉在城市里的变化,除确定每公顷数量阈值外,还建立栖息地模型进一步分析驱动野生动物发生变化的机制。
“我们发现,貉不需要大片的森林和绿地,影响它们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灌木丛和水源。它们还喜欢中小型的公路,白天公路上车来车往,夜里就成了动物们的‘高速通道’。”赵倩倩是王放团队的一员,她前前后后共为5只貉戴上有定位等功能的颈圈。
在不妨碍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城市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对野生动物“进城”保持着很大程度的容忍,不仅帮助闯入村庄的东北虎回归山野,还承受了大象“观光”造成的数百万元经济损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举措。据王放介绍,2020年7月,上海市一个小区的数十只貉群体性行为失常,造成很大干扰。为此,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将小区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
王放还表示,解决野生动物“进城”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保留城市缓冲带,尽量减少野生动物与城市居民的直接冲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野生动物管理永远没有最优方案,冲突会一直存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续调整。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量探索,经验异常珍贵。”王放说。
林业专家支招,市民遇到野生动物时应保持冷静,不要恐吓、逗弄野生动物,也不要喂食。正常情况下,野生动物会主动避免与人类的直接接触。如果在森林公园、山区等户外场所遇到野生动物,请保持正常速度走开,避免快速奔跑惊扰野生动物,不要为了拍照而过分接近动物。如果野生动物误闯入家中,首先打开门窗,让动物有自行离开的通道,如果长时间逗留在家中,可以向当地林业部门和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综合新华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