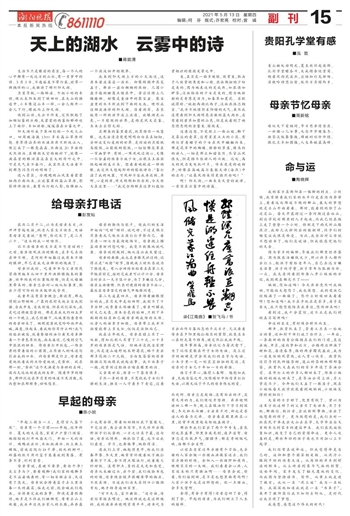■彭发灿
农历二月十二,以为是母亲生日,兴冲冲拿起电话,祝老人家生日快乐。电话里母亲笑着说:“崽啊,你记反了,是二月二十。”这头的我一时哑然。
记不准母亲的生日是不可原谅的!之前,母亲迎风流泪的眼疾,左手无名指屈伸不顺,是何时开始躲过我原本不错的眼神,早已是我无法释怀的愧疚了。
母亲怀我时,吃着爷爷与父亲顶风冒雨用板车从四十里外洪桥镇拖来的薯渣。幼年的我对红薯饭特烦,怕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母亲总会耐心地从红薯里,剔出少得可怜的白米饭供我食用。
我童年没有零食概念,要说有,那也得到山野树林、广袤的农村大地去自我挖掘、自我开发、自我创造。但在记忆深处,我是吃过精致零食的。那是在我大约四五岁的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从城里检查身体的母亲回来了。她刚进屋就笑吟吟地冲我喊,满崽,快起来,看我给你买什么咧!我飞快钻出被窝,就着昏暗的油灯看见母亲捧着一个黄色草纸包,尚未凑近,已嗅到空气中浓浓的甜香。待母亲打开纸包,一堆金黄的带着棱的小团团,正用诱人的味道勾引出我的口水。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慈爱地抚着我的头怜爱地说,是蛋糕。就在那一刻,“蛋糕”这个充满爱与香甜的名词,深而久远地刻进我的生命。随着年岁的增长,那种沉淀在岁月里的味道不见消散,反而愈加浓郁醇香,回味悠长。
母亲的勤快与能干,使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吃好”倾斜。说吃好,不过是偶尔买条鱼或几块水豆腐打打牙祭而已。每月逢一四七为泉湖赶场日,母亲挽上腰篮动身时问想吃啥,我毫不犹豫地说吃鱼。母亲说到做到,她从没让我失望过。
母亲的要强,我也是亲眼见识过的。记得正是“双抢”时节,傍晚收工时队长说为了抢进度,有八分田的水稻要求在第二天早饭前割完,按时完成者可以计六分。母亲当时出工一天才值六分,为了多赚这几分,母亲主动请缨。队长对瘦弱的母亲不放心,最后在母亲坚定的语气中勉强同意。
第二天凌晨四点,母亲领着睡眼惺忪的我,在月光中走向田野。我割不了十多分钟,就靠着禾垛睡着了,母亲叫醒我时天已大亮。原本金色的稻田,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和已被母亲码成堆的禾垛。从旁人的话里才知晓,母亲带上我并不指望能帮上多大忙,仅仅是壮胆而已。
就在去年秋天,母亲在镇上买了一双鞋,得知比别人买贵了二十元,六十多岁的母亲很是气恼。但她并没找店家理论,而是漫山遍野地釆野菊花,晒干卖出那多花的二十元钱。当白发苍苍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跟我说起这事,我不由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抹去噙在眼里的泪。
父亲离世后,母亲一下苍老很多。
孑然一身的母亲,不愿扰乱子女们平静的生活,独自一人守着乡下老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几次看着母亲在夕阳里越拉越长的剪影,就莫名当心在时光某个转角,被突然拉成地平线。
随年事渐高,母亲记忆力每况愈下,为了记住星散在外子女的电话,没上过学的她硬是学会写我们的名字与电话。小本子里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笔迹,是母亲对子女几十年如一日的牵挂。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尴尬如我者,无地自容之外,仅限瞎忙中给母亲打打电话,以期无玷于平凡的母亲伟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