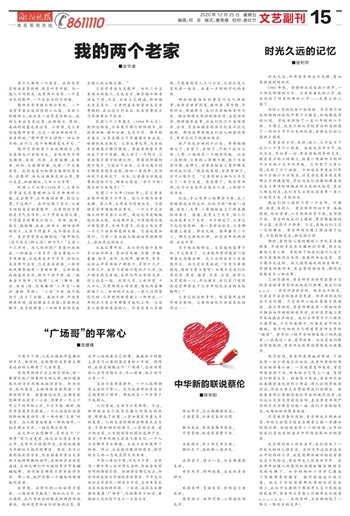■曾利华
时光久远,但有些东西永不生锈,譬如某段深刻的记忆。
1980年秋,懵懂的我还未满六周岁,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把我送进了村里的西岭小学——我要上幼儿园了。
西岭小学的校舍十分简陋。尽管两个砖瓦结构的四合院中有不少教室,但勉强能用的六间,学校安排给了一至六年级的六个班。不得已,校长只好从学校旁边的湾村借了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民房,安顿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民房呈长方形,简陋,狭小,几乎容不下我们二十多个小朋友。地板也凸凹不平,坑坑洼洼,用扫帚一扫,便会扬起刺鼻的尘灰。教室前方的土砖墙上,挂着一块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小长方形黑板,已然裂了几条小缝,还脱了不少油漆。不知道是考虑我们年幼个子矮小不方便坐,还是学校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的课桌椅,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课桌竟然是4条用枞树做成的长长的大板凳,更让人难忘的是,我们自己必须从家里带一条小小的凳子来,才能安坐。
教我们幼儿园的只有一个老师,代课的,姓曾,本村人。曾老师年约四十岁,高高瘦瘦,白白净净,八子胡须经常不剃,显得很干练。曾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常穿橄榄绿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在给我们上完一天的课后,曾老师的衣服上便沾满了红色、白色的粉笔灰,拍也拍不掉。
那时,农村幼儿园的课程小学化是普遍现象,开设的多是算术课和识字课,偶尔也教唱几首儿歌。学校除了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薄薄的作业本外,连教科书也没有。更不像今天这样,幼儿园有嬉戏的游乐场所,有精美的教科书,有益智的绘画本,课间还会配发点心和水果。
上识字课时,曾老师常用伴有浓厚方言的普通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读a、o、e……曾老师读拼音时,发音也不标准,尤其是平舌音和翘舌音更甚。但年幼的我们分不清对错,只是很开心地扯着嗓子跟着读。每次带读时,曾老师都会拿一根细细的竹鞭指向所读的拼音字母,同时在黑板上有节奏地敲出声响来。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根本不看黑板,只是仰着脖子,盯着民房中的木楼板,使尽吃奶的力气跟着曾老师大声的“喊读”。整齐划一的声音响彻在狭小的民房里,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往往是我们跟读得越起劲,曾老师也就带读得越发兴致盎然。
很多时候,曾老师在黑板前带读,下面就有一些小朋友拉拉扯扯,或者叽里呱啦争长论短讲着小话。一旦被曾老师发现,曾老师便会停下来,用本地方言骂上一通,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倘若骂不奏效,曾老师还会扯着课堂违纪者的小耳朵,将人拉到黑板前罚站,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带我们读课文。每每看着耷拉着脑袋面红耳赤的被罚站者,我们往往又会笑得前俯后仰,直至曾老师用严厉的目光对教室扫射一遍,我们才会收起笑容,知趣地继续跟着他读。
尽管教学条件简陋,曾老师也非科班出身,但他总会想方设法在课堂上搞一些诸如默写比赛、分组诵读等小小的活动,让年幼的我们在欢乐的海洋中尽情汲取知识的营养。
就在那间狭小的民房中,我们结束了一年时光的幼儿园生活。当许多年过后重返深山中的西岭小学,我发现那些破旧的校舍再也觅不见踪迹,曾老师也已经逝世多年。在改革开放暖人的春风和创建合格校强劲东风的吹拂下,如今的西岭小学早已建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学设施也日臻完善。驻足于学校前面那光滑的水泥篮球场上,我似乎又看到了那间早已觅不见踪迹的民房中,曾老师正拿着小竹鞭带我们读着a、o、e、i、u、ü……我的耳畔,又依稀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欢乐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