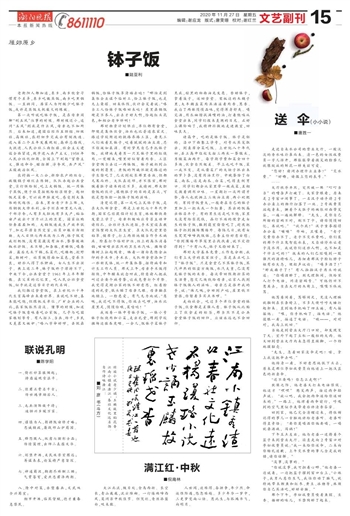■陆亚利
老衡阳人都知道,东乡、南乡饮食习惯有个差异,东乡吃甑蒸饭,南乡吃熏锅饭。一直纳闷,居家人为何极少吃钵子饭,或许是蒸饭太耗柴火的缘故。
第一次听说吃钵子饭,是在母亲闲聊“刮五风”往事的时候。那时候还小,追问“五风”到底是什么风,母亲也不知所然。后来知道,建国后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村初步完成公有制改造。进入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全国上下刮起“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政治狂风。
农村搞一大二公,拆除农户的灶台,收缴锅子砸烂去炼钢,队队办起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上大锅饭。统一用钵子蒸饭,便于社员按配给标准领食。起初饭足菜香,可以放开肚皮吃,感受到大集体的优越性。后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谷子烂在田里无人收。干部浮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稻谷亩产放出十万斤以上的卫星,国家征购任务层层加码。大锅饭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加之旱涝自然灾害,社员口粮日渐短缺。大人日供七两米改为三两,钵子饭变成烂粑饭,没有菜蔬没有油水,餐餐酸辣椒水拌饭。米不够,加杂粮,煮稀饭,喝斋汤。最后无米下锅,瓜菜代,吃糠粑,挖野菜,勒树叶。社员饿得面如菜色,营养不良,好些人得了水肿病,女人生不出孩子。熬上近三年,钵子饭终于撑持不下,中央下令,公共食堂于1961年上半年解散。在父辈的记忆里,吃人民公社食堂饭,似乎就是过苦日子的代名词。
我们躲过食堂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来看世界。虽说吃不好,基本能吃饱,但跟机关单位、厂矿企业的人比,农家饭依然清淡。懂事的时候,知道吃钵子饭意味着吃公家饭,几乎与吃国家粮划等号。有人招工、当兵、转干,乡民又羡慕又嫉妒:“咯八字命好啰,丟脱鼎锅饭,恰钵子饭享清福去哒!”哪怕是到集体企业谋个临时工,恰上钵子饭,也是无上荣耀。回来休假,伙计会笑着说:“咯当工人恰钵子饭咯回来哒!屋里鼎锅饭硬是不养人,出去才好久啊,恰起红头花色,和相公老爷样咧!”
那时物资计划供应,单位都有食堂,即便是集体伙食,油水也比普通农家足。路过学校附近的铁路养路工区,看见工人们端着瓦钵子,咬着腻腻的油豆腐,忍不住涎如泉涌。有时梦见自己手托钵子饭,放肆地夹着另一只瓦钵子里的红烧肉,一觉醒来,嘴里好似留着肉香。工区食堂偶尔丢过一两钵饭,钵子被扔到山坡的刺蓬里。煮饭的阿姨怀疑是路过的学生偷吃了,几次到校长那里告状,但都无果而终。大队在近郊,并不很穷,那时饿着肚子读书的还不多。我猜测,那大胆偷饭的伙计,填饱肚子的目的是其次,可能是想体验一把钵子饭的滋味。
清楚记得,第一次吃上瓦钵子饭,是在大队部食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妹妹都快要发蒙上学了,母亲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结扎。公社计生队进驻,手术室设在教室隔壁的大队卫生室。在大队礼堂里垫稻草、铺席子,打上两排地铺当作手术病床。阶基打个临时炉灶,灶上的高压消毒锅,嗞嗞喷出浓烈的卫生水汽味。操场苦楝树上扯起绳索,晒着一溜白色隐含血印的手术巾、手术衣。大队部食堂添加了一些新瓦钵,统一开集体餐,招待病号和计生工作人员。那天上午,母亲手术做得轻快,中午醒来就念叨我,特意请人把我叫过去要个病号餐,让我免费打个牙祭。我觉得是蹭公家的饭不好意思,红着脸进的礼堂,低头瞄了母亲几眼。母亲躺在地铺上,一脸慈爱,有气无力地说:“崽呃,我还吃不得饭,你端去吃啰,油水比屋里足,慢慢恰哦,莫噎哒!”
我端着一钵中号钵子饭,一钵小号钵子红烧肉和小菜,走出礼堂,蹲到学校操场边狼吞虎咽。一会儿,饭钵子菜钵子见底,棕黑的釉面油光发亮。沓好钵子,拿着筷子,送回食堂。案板边的木桶子里,大半桶盐菜肉沫汤溢着肉香、葱香。我舀了两钵慢慢品味,觉得浑身舒爽。喝完汤,用衣袖揩拭满嘴的油,打着饱嗝从食堂出来,同学们投来羡艳的目光。正好上课铃响了,我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回味良久。
读高中,吃的是钵子饭。钵子是铝的,沿口下面錾上学号,对号从蒸笼取出,到桌席分菜吃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立高中住校生按三两米一餐缴米,另缴菜油两斤,每学期学费和菜金四十多块,伙食自然极差。早上也吃干饭,菜一成不变,是从酱菜厂的大坛子抓出来的萝卜条,没有用油烹炒。中晚餐除了白菜、南瓜,还是南瓜、白菜,吃得直倒胃口。同学们都会从家里带一瓶咸菜,互相交换着调剂口味。一星期打一次所谓牙祭,每人也就摊上三块油豆腐、两小砣肥肉。男同学饭量大,一般要在自己的钵子里加上一把米或一个红薯,蒸出的饭高出钵沿半寸。有的男生还是吃不饱,家里又没有给零花钱,品行不端的便拿走女生的钵子饭,躲到寝室偷偷吃了,趁夜把钵子扔到操场围墙外。每隔几日,就有女生哭哭啼啼找饭钵,总务主任好意安慰:“你到围墙外草窝里去找找看,说不定捡得到!”十有八九,钵子又捡回来了。
那时大学基本免费,工作包分配,我们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算是真正吃上了“钵子饭”。只是食堂已不蒸钵子饭,蒸汽冲熟的铝盒方块饭,水汽太重,已没有瓦钵子饭的米香。每次带回假期折算的生活费,想交几块钱给母亲,让家人找到钵子饭傲人的滋味。母亲总是推开我的手,说:“徕几呃,分田到户哒,屋里钱不紧张,你留着多买点书啰。”
走向社会,吃过多个单位食堂的钵子饭,伙食都是差强人意。钵子饭从此贴上了伙食差的标签,那当然不是公共食堂钵子饭的回归,应该永远也不会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