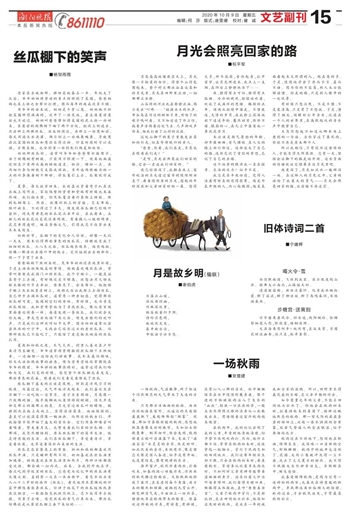■杨邹雨薇
老家在古城南郊,耕田菜地各占一半。年纪大了之后,爷爷奶奶将劳动的重点转移到了菜园,爸爸妈妈也在上班之余帮忙打理,因而每年的收成还算不错。
用爷爷的话来说,奶奶是个贪心鬼。奶奶她不但把菜园种得满满的,还开了一些荒地,甚至连屋前屋后也不放过。奶奶叫爸爸帮忙将菜园的泥土挑一些回来,在屋前的刺槐树下砌了两个方坑,把泥土倒进去,然后种上两颗丝瓜。丝瓜的周边,再种上一些葱和蒜,每天用淘米水浇灌,偶尔倒上一些鸡粪鸭粪,导致葱蒜比菜园的丝瓜和葱蒜长得还好。炒菜时随时可以采摘,方便至极,也令村里一些村民们艳羡和效仿。
奶奶种丝瓜时,通常叫爷爷和爸爸帮忙搭架子。由于刺槐树有树枝,只需用刀修理一下,使离地面最近但至少有两米高的树枝通直、粗壮、稀松一点,再用细竹条与树枝交叉搭成网状,另外选两根略为粗一点的竹条挨着树干绑好,将瓜蔓引上去,瓜架就形成了。
夏季,每天放学回来,我就喜欢拿着凳子趴在洗衣板上写作业,家住隔壁的堂哥和堂妹有时候也来凑热闹。我们抬头望,但见瓜蔓沿着竹条爬上树枝,爬到瓜棚架上。然后,就像织机上的穿梭,交叉布局,绿叶疯长。不记得过了多久,便发现丝瓜棚已经绿叶密织,间或有黄色的丝瓜花次弟开放。在我看来,五瓣儿的丝瓜花比菜花还要明艳,有着摄人心魄的明黄,花蕊黄得透明,极具秀雅之气,引得我忍不住拿出美术本来写生。
初秋时节,瓜棚下的变化令人惊讶,好像一天比一天大。原本记得那些黄色的丝瓜花,转眼就变成了细细的丝瓜。七八天之后,丝瓜越长越长,越长越粗,仿佛一群潜伏在绿叶中的战士,突然接到出击的命令,便一下子冒了出来。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时,见爷爷奶奶还在地里忙碌,于是主动承担做饭菜的事情。妈妈喜欢喝丝瓜汤,常常叫爸爸或我摘门口的丝瓜。我个子矮小,一般是站在凳子上去摘,有时候还是不够高,就想法用火钳或晾衣服的竹竿去牵扯。爸爸见了,会来帮忙,他把梯子搬上洗衣板靠在树上,扶稳之后让我爬上去摘丝瓜。自己伸手去摘丝瓜时,通常有一种亲切感,觉得那些丝瓜好可爱,能闻到它们的香味。有时候,也为寻觅丝瓜烦恼。我和堂哥堂妹为了寻找丝瓜,像从老百姓里面查巡特务一样,每逢发现一条丝瓜,我们就会大惊大喊,争先恐后地摘下来之后,便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只是我们这种欢呼似乎太早,因为奶奶通常从密密麻麻的叶子中,又找出已经长过头的老丝瓜来。而那种丝瓜已不能吃了,只能除了皮壳做洗碗筷的丝瓜扎用。
夏夜和初秋之夜,天气炎热,村里人喜欢在户外乘凉乃至睡觉。爷爷通常将靠椅搬到丝瓜棚下点燃蚊香,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我本来最怕烟味,但又无法拒绝故事的诱惑,便与堂哥堂妹经常围绕在爷爷的跟前。爷爷讲的故事很精彩,通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笑的时候,感觉整个丝瓜棚也在发笑,那些黄色的花朵,跟着我们笑着笑着便成了丝瓜。
丝瓜棚下最美的应该是夜晚,特别是凉风习习的秋夜。白露过后,天气开始凉爽起来。我们喜欢坐在凉棚下一边吃饭一边赏月。房子坐东朝西,月亮像一只狡黠的猫,蹑手蹑脚地从屋顶移到树梢,悄无声息却是那么的圆那么的亮。月光穿过丝瓜叶的罅隙,投射到洗衣板上或地上,显得温温柔柔、斑斑驳驳的,甚至可以说温柔得像一幅油画。而附近的秋虫们,早就按捺不住开始了盛大的音乐会。它们用各种嗓音叫着唱着,赞美着月光,也赞美着我们家的丝瓜棚。刹那间,我忽然醒悟到,原来丝瓜棚下的简单生活,就是诗意般的生活。我们在丝瓜棚下,享受着清凉,享受着收获,也享受着简朴而美丽的生活。
丝瓜是农家餐桌上的常客。奶奶和妈妈都喜欢用丝瓜开汤,只是辅料有所不同。奶奶喜欢在丝瓜汤里加鸡蛋,妈妈喜欢在丝瓜汤里加肉片,两种口味都很受欢迎,都会被一扫而光。后来,当我到外地求学,每次吃到学校里的丝瓜,总感觉与记忆中的丝瓜汤有天壤之别。直到有一次在一本画册中,看见齐白石老人八十三岁时的画作《丝瓜》,看见他用焦墨挥就的竹篮中横陈着数条丝瓜,惊讶于他笔下的丝瓜纹络线条浓淡相宜,一股勃勃生机跃然纸上。忍不住用手去抚摸,用鼻子去嗅,感觉丝瓜的青气扑鼻而来,那丝瓜仿佛就是从屋前瓜棚上垂下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