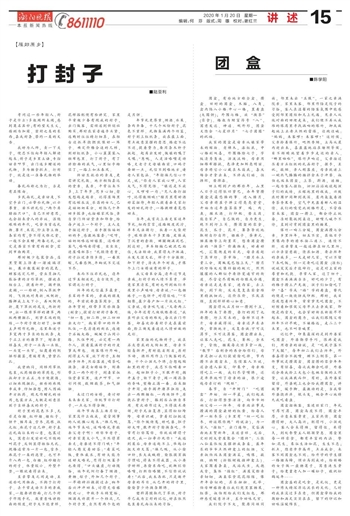考问过一些年轻人:封子是什么?多数闻所未闻,感到莫名其妙;有的望文生义,猜测为加固、密封之类的东西,甚或封条、禁约一类的文告。
我好为人师,卖一下关子,便忍不住向年轻人解读起来:封子是乡里土语,专指访亲叩节、出门返乡赠送的礼物,多为糖食糕点。打封子,就是这一准备礼物的举动。
备礼而称之为打,当是有其缘由。
乡民尚礼,走亲访友,不空手出门,必带些礼物,以示尊重。若不讲礼信,“两个肩膀抬只口”,自己不好意思,也会招来旁人的非议。温饱艰难的年代,吃食为首选礼物。薯片、米花、炒豆等土物,各家均有,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不会互赠。所备之礼,必定是居家不常有的副食,需到市面购买。
那时极少包装食品,店里货架上排着一溜玻璃凉缸,展示散装副食的花色。顾客选定几样,营业员抽几张谷黄的方形草纸,摆放在柜台上。提着杆秤,揭开铁皮桶,一一称好,倒入草纸中间。飞快地对角折、双侧折,腾挪成上大下小,再双侧内折。覆下草纸的尾尖,内折封口,扯一根席草样的撸草,两纵两横捆扎,别紧末端的绕结,一个封子便打好了。如顾主声明作礼物,店里奉送寸多宽两寸多长的红纸条,夹于正上方的撸草下,增添吉祥喜庆。封子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宽一头窄,似覆着的倒梯形撮箕,有棱有角,紧紧扎扎。
我曾纳闷,同样用草纸包裹,从药铺捡的草药包,形状却方方正正。为方便提携,以细麻绳捆扎,粗些的麻绳串成串。仔细推想,因人因病开方抓药,绝无作赠礼的功用,包装方正,大概是刻意区别于吉祥喜庆的封子。
封子里的花色不多,无非是白糖、红砂糖、糖粒子、饼干、猫耳朵、雪枣、花根、状元红、麻花寸这几种。封子表达礼尚往来的心意,包装过大,寓意打发前世吃不饱的叫花子,反倒显得粗俗无礼。规格通常为一斤一包,雪枣、麻花寸一类的泡货,也可半斤八两一包。白糖、红砂糖打的封子,体量较小,外壁平整,一眼就看得出来。
至亲挚友之间走动,互送些吃用物品,不拘于打封子。去平常走动不多的亲戚家,一般要讲脸面,打几个封子作随手礼。数量意味讲脸面的程度,封子又不能重样,花样搭配便有些讲究。家里平常极少备有现成的封子,出门做客,需顺道到供销社购买。那时农家普遍手头紧,选购时往往精打细算,在柜台边抓耳挠腮犹豫好一阵子。确定价格合适的几样,别好红纸条,小心翼翼装入粗布包里。打了封子,有了讲脸面的底气,心里似乎踏实了,一路上如沐春风。
拜访生疏些的亲友,更需讲究礼数。地方相隔甚远的堂亲、表亲,平常往来不多,上了年岁,思乡心切,愈发想越走越亲。记得屋场里有远嫁辰溪、乐昌的女儿,已是姑奶奶辈分,时隔几十年回乡探亲,也按娘家风俗,亲自登门拜访堂亲和邻舍,给每户送上一个封子。主人左手接过封子,右手握住姑奶奶的手,感激地客套:“哎呀,姑奶奶咯远回娘屋,还咯讲客气,咯吗要得噻。坐坐坐,进屋喝杯茶!”礼轻情意重,封子拉近亲情乡情,一番寒暄,几番感慨,半晌说不完道不尽。
来而不往非礼也,逢年过节互相送礼,自古使然,老家谓之打封子。
拜年的礼信最多最重,长辈的平辈的,亲戚的朋友的,年前就要盘算周全。置办年货时,顺带多买些换杂(副食),提前打好封子备用。“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出大行”。拖家带口的拜年队伍,一色清透的新衣,迤逦于石板大路,蜿蜒于山间小路。队伍中间,必定有一两个人,提着装满封子的竹皮箩或布包。迎客爆竹炸响,到得主人家,放下封子,互相拱手拜年,然后落座,喝茶吃换杂。若是女婿姑爷,则要带上一两个封子,到妻家叔伯堂亲家里,逐户叩节。口彩问候,敬烟敬茶,和气融融。
未过门的女婿,要讨好未来岳丈家,传统节日打封子,一点也不得含糊。
端午节尚在上滩月份,家里没什么收成,爱管闲事的人就操心起来:“徕几呃,端午节来哒,送吗咯礼孝敬岳父老子啊?劝你爷老子,对亲家莫太小气,不然得罪岳丈,老婆进不得门哦!”年轻人憨笑着回答:“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好大能力送好大咯礼,冇得打双寡手也要得。”口头谦虚,行动随俗,端午礼例行备了烟酒、黄糖、粽子,外加几个封子。一早精神抖擞提过去,晌午后兴冲冲回来,讨得丈母娘的欢心。中秋手头稍宽裕,烟酒或许提升一个档次,几个封子里,自然有两个包的是月饼。
年节礼更厚重,烟酒、水果、条肉齐备,十几个双份封子,花色不重样。礼物集满两个竹篮,封子别上红纸条,放在最上面,有点故意显摆的意思。路途不远不近,提着费力,要用杂木杆子挑起。起肩出发时,做娘的嘱了又嘱:“崽呃,人是活咯嘴是动咯,丈老子丈母娘面前,口码子要甜一点,礼信不到咯地方,请老人家包涵。”年轻徕几信心十足,说:“你老人家放心啰,人家大气,不得见怪。”娘还是不放心,又啰嗦一句:“见人要打招呼,记得散烟哦!”腊月里有好酒好菜招待,年轻人提着岳丈家打发的回礼封子,一路微醺着晃悠回来。
当年,我首次上岳丈家送年节礼,细雨霏霏,道路极度泥泞,单车无法骑行。驮着一大袋封子,艰难推车十多里路,皮鞋成了沉重的套鞋,裤腿糊满泥巴。到达时,单车轱辘已被泥巴粘住,无法转动。我累得大汗淋漓,头发又湿又乱,样子十分狼狈。卸下封子,清洗半个时辰,才像个上门女婿该有的样子。
我父母辈分高,逢年过节走亲戚,打封子的人情不算重。毕竟家里清寒,有时也听到他们半夜里小声嘀咕。母亲说:“一包糖珠子,一包饼干,对得住哒。”“不相像,最少每户加一斤状元红。”父亲说。母亲叹气道:“又要两三块,今年还有几块钱账要还。”我虽听出父母的难处,每次出门作客,却喜欢拎着封子走在最前面,脸上焕发着通达人情世故的光彩。
家里接的礼物封子,放在石灰垫底的大陶缸里。母亲不轻易拆开,有时能省则省,原封不动,循环用作上门做客的礼物。十个小孩九个馋,念想起陶缸里的封子,我忍不住咽着口水。起初胆子小,不敢开封,揭开盖子,俯下身子,闻一闻混杂的香味,望梅止渴一番。后来脑子开窍,动手揭开撸草扭结,夹出一两颗糖粒、一两块饼干,原貌扎紧封子,躲到后山独自享用。有次动作过大,不得技术要领,封子无法复原,显得松松垮垮。母亲识破,拿着烂扫把追骂:“你个饿佬鬼、好吃婆,胆子好大呀,敢开封子偷换杂吃。平常冇打你骂你,你就放肆得寸进尺,我一扫帚扑死你!”我逃到屋后,母亲追赶不上,举起扫把又劝又骂:“徕几呃,从小偷口针,长大成贼精。偷张摸页搞习惯哒,将来不得成器。从小要学好样,再偷东西吃,就撕烂你咯嘴,打断你咯腿,不信你试试看!”此后,我未再犯,只是避开母亲的耳目,从已开的封子里,偷偷拿少许换杂解馋。
塑料薄膜取代了草纸,封子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好在依然包裹着礼尚往来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