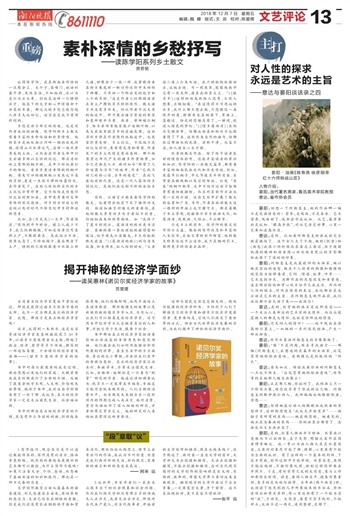晏阳,当代著名画家,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意达,省作协会员
晏阳:回想一下珂勒惠支,她的作品哪一幅不是充满情感的?营养,是吸收,不是吞食。艺术营养,吸收好了,逐渐会形成认知。从艺,最重要的是认知。“眼高手低”,对从艺者是好事。心里一定要知道高水准。
意达:是的。比如看珂勒惠支的画我就完全被震撼住了。这个女人太了不起,她的《饥童》和《面包》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杂志上看过,孩子瘦弱饥渴的眼神和母亲因心碎而转身哭泣的背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晏阳:珂勒惠支是我最敬仰的女画家,她以极其简括的造型、极具个人特质的构图和超强的视觉张力诠释着爱、悲悯 、愤懑、抗争、呼号……艺术走到今天,消解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重量感,追求明丽轻快和赏心悦目似乎已成主流。然而对人性的探求,对内在情感的表达,永远都会是也应该是艺术的主旨。在珂勒惠支的作品前,我们永远都不会无动于衷——我深信!
意达:是的,欣赏她的画正是这种感受——一个关注人类命运的艺术家的大情怀。而往往能震撼人的都是大情怀,也就是你所说的情感。
晏阳:悲天悯人的情怀!——地平线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一如她的一系列农民组画,产生一种压抑感。
意达:你用水墨画珂勒惠支的肖像像极了。
晏阳:“像”不是问题,难在寻找语言——那幅《珂勒惠支》,我塑造的是暮年的女画家,让笔墨有她的绘画意味,连构图也是标致性的“珂式”。
意达:原来如此。难怪我看你画的珂勒惠支一点也不陌生。“让笔墨有她的绘画意味”,你参考的是她那几幅自画像么?
晏阳:正是那几幅,你说对了。我的画上只一个特写头像,动态就参考了你说的这几幅。珂勒惠支的眼神很打动人,我却偏偏让她眼睑低垂,冥想……
意达:你将她最打动人的眼睛画成低垂的冥想样子,这种构思便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她脑子里所有的东西——她在构思的,她看见的,她正在准备画的东西……你的画里全都有了。没画反而又全画出来了。
晏阳:是的,水墨人物画并不好画。水墨画以意胜而不以状物长,至于光影、明暗之类外在因素惯常略之。我一贯以为画人物尤其是水墨写意,总要对对象尽可能了解、理解,心里要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下笔才有数,创作过程中才能审视。水墨写意,离照片越远越好,不独形象处理,绘制过程同样要丢开照片。于是,有时寥寥几笔的大写意,案头工作却要很长时间。读史,查阅人物生平,搜集形象素材,更多的是体味与揣摩。当年画《两个画家》时,我阅读了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版本的齐白石、毕加索传记和有关资料,待心里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的“我”,才动笔。大写意,落墨不需多耗时,个把钟头;大画不过一两天,连同整理,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