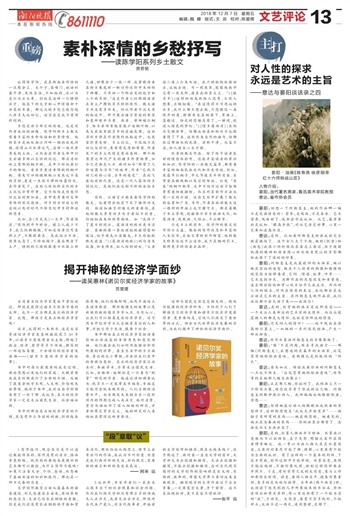认得陈学阳,是在衡南县作协的一次聚会上。大个子,豪嗓门,说话利落干净,爽快直接,不知他的,还以为是位北方大哥。但就是这样一位铮铮汉子,他笔下的文字和心中情愫却十分柔软丰盈,那淡淡的乡愁总能勾起人许多久远回忆,这实在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乡愁是游子命定的伤逝,也是写作者永恒的话题。陈学阳的乡土散文有着丰富的生命体悟和朴素情感。他的家乡是地处湘江河畔一隅的近尾洲镇,深得山川水泽之气。这样一块风景秀美的土地,必然会在作者生命中衍生出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湾湾岭岭上葱郁的桐子树,是年少时玩耍打斗的场地。母亲手里清香绵软的桐叶粑、滑爽可口的酿辣椒以及来之不易的月饼,更是一生抹不掉的味蕾时光。在作者笔下,这些儿时纯粹自然的乡土记忆非常珍贵。它不仅仅是伤感怀旧之后的附加品,其中更有着对生命苦难的深沉感悟、对乡村古旧道义的追惋以及对时代不断变化中乡村命运的思索。
比如,在《月光光》一文中,作者写道:“很快到中午时分,墟上人减少不多,我已饥肠辘辘,可知道母亲还冇卖掉土产,不敢提要求。见我站立不安,母亲也急了,不停地揩汗,最后贱卖了土产,挣到的几块钱蘸着口水数上好几遍,好像会少一张一样。我紧跟母亲在街头巷尾新一轮讨价还价中来回转了两圈,只买回一个刚出笼的包子和三个麻月饼。”这是作者儿时跟随母亲去卖土产攒钱买月饼的情形。散文语言并没有多华美,但从作者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语言背后的寒苦和某种艰辛力量。再者,帮婶娘打桐子、给乡亲邻里挨家挨户送桐叶粑、以及大家庭里敬月半的虔诚氛围,这些淳朴乡情在作者隐约地叙述中,也更显珍贵美好。乡土记忆,不仅仅只是回忆与怀旧,更要有反思和希望。作者笔下的乡土风情是有痛感的。那个物质贫乏年代产生的诸多珍贵物事,如今已是物是人非。面对如今“附带了几许喧嚣与浮华”的城市,作者“已找不回儿时的心情,当年的感觉”。在此飞速向前时代里,这是一代人集体的乡村记忆,是他们永远割不断的永恒乡愁。
同时,从语言方面来看陈学阳的散文,也看得出他是下足了锤炼功夫的。他深知语言对散文的重要性,在他的散文里有许多句子看似不经意,但细细品来却别有韵味。如“或许少了夏日的闲云,莲湖湾的秋水更为清澄。柔澈的每一条纹理把秋藏得愈加深远,似乎要先打湿睫毛,才允你把秋瞧足滤透。”(《莲湖湾的秋》)词句清爽疏落、和美绵长,拟人恰到好处。“父亲接二连三打来电话,我只好把钱纸搭回去,让他去烧。可一到夜里,朦朦胧胧中总有一丝灰烬,落在我的鼻尖上。”(《敬月半》)这样的结尾既给人思考,又促人想象,且极切题。“在这慢得不可思议的水乡,我什么都不想去做,只想握住一朵慢开的莲,静静呆坐在树荫下、草滩上、篷船边。纷乱的思绪没有了,一瞬间,就进入绿色的梦幻。”(《慢乡莲湖湾》)长短句交错排布,仿佛这些柔和的句子也跟着慢了下来。这些优美自然的语句,仿佛经过那湘水的洗涤,清新干净,从容不迫,令人读来心生宁静。
优秀的散文作品,除了给予读者良好的情感体验外,还能丰富读者的常识和知识。陈学阳的一些散文篇章,都有着丰富的湘南民俗文化和历史传说。例如,寒露节打桐子、中元节敬月半供老客、家常食品酿辣椒以及它的传说、打发“老客”的桐叶粑等。文中不仅对这些习俗场景有着细致描绘,而且对其制作方法也有一定的介绍。这些无形中扩展了散文的容量和广度。另外,作者在旅游散文这一题材的开拓上也可圈可点,都是着眼于本土景观,挖掘推介家乡旅游文化。如莲湖湾、凤凰湖、火焰山、斗山桥等。
行走乡土枕前书。陈学阳的散文创作劲头正盛,勤奋的写作状态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他宝贵的创作财富。他的散文特色远远不止这些,我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读者去品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