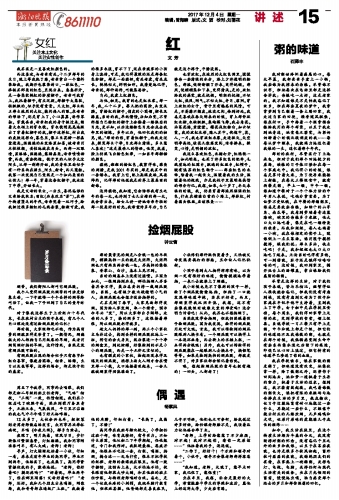我对粥始终怀着感恩的心。每天早晨,我都要亲手煮上一小锅,放些娘为我捎来的杂粮。尽管娘不识字,但她每次在电话里都是这样告诉我:杂粮吃一点好,这是老家的。我不知道娘是不是怕我忘记了故乡,但在那些夏夜的梦中,我常常梦到自己顺着一条土路回家,我走过自家的田埂,稻香随风飘散,娘在村口,手中拎着一个经常捎杂粮给我用的那个布袋,以至于我走到她身边,她竟毫无察觉,与彭奶奶聊着小时候比较调皮的我……每每从梦中醒来,我就竭力地追忆着我娘的一生,追忆着那个年代。
那时的农村,尽管实行了土地承包,但对于我们那个田地较少的屋场,缺粮的日子依旧掺和在每一个家庭之中。我记得小的时候,娘总是算计着大米,为了使存米能接上新粮,在每天三餐饭食中,就有两餐是粥,早上一顿,中午一顿。娘知道中餐对于一个干体力活的中年男人来说,吃饱非常重要。为了让爹不受饥饿,在中餐的那顿粥里,娘总是要放些杂粮,如晒干的山芋角、南瓜等。我看到爹端着青边蓝海碗,碗里的杂粮多于米粒,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在吃一顿特美的佳肴。而我和姐姐,每人也端着一小碗,放在娘指定的凳子上,随娘倒上一点点菜汤。娘用筷子搅拌搅拌,跟我们说:那么多油,快点吃吧!于是,我和姐姐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无论当时吃得有多饱,可一到傍晚,肚子还是饿得咕噜咕噜的叫,这时候,我回到家里,揭开灶台上的汤罐盖,拿出娘给我们盛留的稀粥。
尽管是这样的生活,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苦与乐相比,短暂得让人很快就会忘记,但我们没有考虑到娘,没有考虑到父母为了孩子和家庭在半饥半饱中支持着,直到我上了中学。由于初中是在学校里食宿,每个周末,我们得回家带上足够的米,交到学校的食堂,领上饭票。虽说学校一日三餐只有早上是粥,中午和晚上都是干饭,但它们的味道远不及我娘做的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依稀感觉到生命中有些东西像水退之后留下的痕迹,即使已从心田上流过,但它特有的味道早已渗进了你的血液。
我在学校读书,娘在家做的粥更稀了,但味道没有改变,她像往常一样,除了做粥之外,还劳作于田间地头,她和爹一道执着于生存的努力,执着于生活的追求。想到这,我不禁肃然起敬。我吃着娘做的粥长大,娘把有限的米粒均匀地安排在生活的岁月里,熬成糊状,让日子迂缓地富有耐心地绕过一些什么,再绕过一些什么,不经意中绕出村庄的几缕炊烟,几声鸡鸣和犬吠,让原汁原味的爱绕满儿子成长的经纬……
如今,我生活在城里,在这个物质生活颇为丰盛的今天,我没有断掉对粥的怀念,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故乡和我娘,以至于在某些夜晚,也许是很多个秋风初起,窗外秋叶瑟瑟的夜晚,我谢绝朋友们的宴请,在家熬上一碗稀粥,关掉电灯、电视、电脑,关掉任何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设备,坐在月光倾泻的窗前,慢慢地坐喝,独自感受那个远去的岁月和那份温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