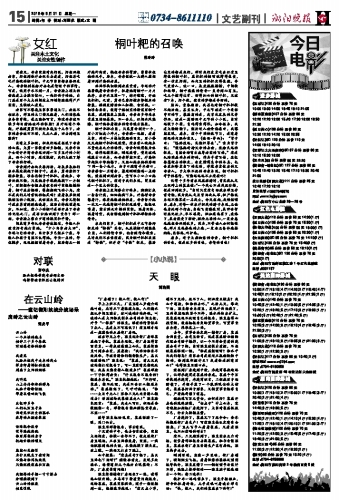关注女性创作
桐叶粑的召唤
肖玲玲
前些天,母亲突然对我们说,好想回趟老家,好想到你外公坟头去看看,好想再吃吃外婆做的桐叶粑。中元节家家都在祭拜先人,母亲特别想念外公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可是,做完手术不到一月,母亲脸上硕大的伤疤看上去触目惊心,一向好面子的她,出门总是用个大大的阔边太阳帽将脸遮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看见。
老家可不像城里家家紧闭大门,老死不相往来,那里的大门整天敞着,人们闲散地在各家穿梭,毫无隐秘可言,难道母亲就不怕乡邻目睹她破碎的容颜?另外还有个难题,外婆随舅舅阿姨迁来城里十几年了,老家的房舍破旧不堪,久无人居,回去到哪里落脚?
虽有太多担忧,但我们还是想遂了母亲的心愿。大舅一家提前回乡拾掇,父亲率两个女婿开车将母亲送回到一百多里外的小村庄。两个小时后,通过微信,我们大致了解了母亲的行踪。
母亲到外公坟头祭拜后,与表弟表妹们在水渠边摘起了桐子叶。原来,舅母磨好了糯米粉浆,准备包桐子叶粑粑。看起来,母亲兴致不错,只见她身手敏捷地摘下一片桐叶,用拇指和食指夹着粗长的叶茎轻轻搓转着,桐叶左右摆动,像翩翩欲飞的小鸟。这不是我们儿时常玩的把式吗?看着表弟传到微信里的小视频,我哑然失笑。母亲又将桐叶放在鼻前深深地嗅着,然后出神地望着远方。不知道,这小小的桐叶是否开启了母亲的记忆之门,是否让她回到了童年?那一刻,母亲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和平静。
间或有乡邻从母亲旁边经过,年轻人和孩童好奇地打量她。“少小离家老大回”,年近七旬的母亲,离开家乡已经五十载,年轻人和孩子自然不认得她。年长一点的,停住腿步,迟迟疑疑望着母亲,然后都无一例外地冲向前,挽住母亲的臂膀,紧紧位住她的双手。后来,母亲便被一大群人簇拥着回到外婆的老屋。
画面很快切换到老屋堂前。年迈的外婆紧拽着母亲的手,拉着她将桐叶一片片洗净,在开水里烫一下,摊开晾晾,开始包粑粑。之前,舅母已磨好糯米掺粳米的粉浆,稍稍发酵后加入红糖、食用碱。一切准备妥当,便将干湿相宜的粉团用桐叶包裹,放到蒸笼上蒸熟,母亲与乡邻坐在堂屋里闲话桑麻。不一会儿,灶间水汽蒸腾,桐叶混合着糯米的清香溢出蒸笼。
桐叶粑粑出笼,只见舅母剥开一个,用小刀切成小碎片。母亲稍一迟疑,看看大家,面对一片热切鼓励的目光,用小餐叉叉起桐叶粑粑送进嘴。这在常人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动作,母亲却做得极为艰难,动作迟缓笨拙,刚送进嘴,嘴角就哒哒流出口水来,而母亲浑然不觉,外婆忙拿起纸巾替她擦了,又贴心地在她的脖颈下围一条小毛巾。由于口腔有手术伤口,母亲禁食一月有余,最近刚刚能喝一点稀饭,没想到回到老家,竟可以小口小口地吃桐叶粑粑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母亲脸上发间渗出汗珠来,渐渐汇成一条条汗线,汩汩地滴下来。外婆帮母亲擦着汗,疼爱地轻拍她的肩,母亲努力地一次又一次地将桐叶粑粑送进嘴,轻轻咀嚼着,露出满足幸福的笑容。隔着网络,隔着时空,我仿佛嗅到桐叶粑粑那特殊的清香。
在我们家乡,桐叶粑粑是中元节祭拜祖先的“特供”美食。从采摘桐叶到蒸熟出笼,人们神情专注,饱含深情和敬意。儿时我们不在意这些,因为桐叶粑粑虽然是“特供”,但并非“专供”祖先,最后沾光的都是我们。那时我们更爱吃在灶堂里烤焦的桐叶粑,裹粑粑的桐呀被烤得焦黄,凉一凉更好剥,而内里的粑粑变得焦脆,香气更诱人,咬一口,表皮脆脆糯糯,中间软和粘绵,桐叶淡淡的清香一直香到心窝里。吃几个糯得沾牙、甜得沁心的桐叶粑,天就凉下来,好个秋,孩童的梦都是香甜的。
然而,青春期后,我再也对桐叶粑粑提不起兴趣,甚至认为,中元节就是一个迷信守旧的节,最恶劣的是,我首次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一篇暗讽中元节的小小说,当时还获了个奖,自鸣得意得很。如今想来,我是大错特错了。经历过人世沧海桑田,我蓦然发现,原来,这个中国传统节日,是有着深远的内涵和意义。《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为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这是从治国层面来剖析的。作为寻常百姓,追忆祭奠逝去的祖先,会更懂得生命的本真,也会更加珍爱当下的生活,孝敬亲爱健在的父母亲人。于大难不死的母亲来说,桐叶粑粑寄予的感情,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吧?
记得十多年前在凤凰旅游时,曾见沈从文无坟碑上的墓志铭:“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当时只觉这句话放在那里非常奇怪,因为沈从文虽曾两次从军,但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一名战士。今天想起,我幡然明白,原来,对每一位在外征战的游子来说,无论他身处哪个行业,当他飞黄腾达时,或许会暂时忘记故土,乐不思蜀。但如果他累了,疲倦了,或者遭受了挫折,飘泊无助的心,一定会急迫地想要回到故乡。因为,不管世人如何轻慢他,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一定会无条件地接纳他,包容他,呵护他。
原来,对于大病初愈的母亲,桐叶粑粑的召唤,便是故乡的召唤,亲情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