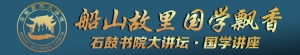“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1689年,野史画家刘思肯为王船山画像时,王船山写了这首《鹧鸪天》,表达了其至垂暮之年愿望仍未了、梦想未实现的悲愤心理。
王船山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未圆呢?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和动力,使他以40余年的漫长人生“活埋”在清朝统治的天地里,誓与清廷不共戴天,孤苦顽强地拼搏到底?
孝忠的家风,使得王船山对朝廷有一种深厚的归属感、认同感
明朝灭亡,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正值壮年的王船山就遭逢明亡清兴这个惨重的历史变故,这对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他来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极大耻辱。
用梁启超的话说,国破家亡对王船山来说,可谓“创钜痛深”;萧萐父在《王夫之评传》里说:“这对王船山是一次极其巨大的刺激”。由此可见,王船山经受的这个痛是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思想灵魂的受苦。
“这只是暂时,明王朝的江山还会回来的”。当时的王船山,显然只是被刺激了一下,并没有气馁。于是,一方面亲自组织和领导武装抗清复明斗争;一方面协助南明王朝抗清。
在三次冒死参劝党人失败、清军又步步紧逼的情形下,王船山痛感孤立无援、壮志难酬,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决计“屏迹幽居”。从永历6年(1652年)起,直到生命的终止,在他的后半生,一直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开始了漫长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著书立说生涯。这个过程,他的精神仍然没有屈服于清朝廷的统治,而是全面解读经典,重新诠释传统文化,试图为民族国家开出一片新天地。
然而,遗憾的是,他生前反清复明的政治抱负终究未能实现,这给他留下了满腔“孤愤”。这“孤愤”留给后人的,却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中的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谈起王船山对明朝廷的感恩之情,这要从其家世说起。
船山先祖本为江苏扬州高邮人。据记载,王船山的十一世祖王仲,跟随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因为军功显赫,被授予千户。十世祖王成,在明成祖永乐初年,因为拥戴明成祖朱棣有功,升任衡州卫指挥同知(三品武官,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氏家族就此搬到衡阳,成了衡阳人,到王船山时已经是在衡阳第九代了。祖先世代以军功显赫,并忠于大明王朝,与大明王朝相始终。可见,王船山一家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功勋卓著、家世显赫。从船山第七代祖公一山居士王宁开始转武习文,“以文墨教子弟”,成为儒学传世之家,家境一直相当殷实。
由此可见,王船山祖上世代都受到朝廷的优待,这使得他对明朝怀有无限的感恩之心。
同时,王氏家族不仅具有渊博的家学,而且有着优良的家风。王氏家族世代家教甚严,形成了忠介刚直、清廉自守的优良家风,孝与忠是这个家族的核心家风。但这种严格并不是一味的苛责,而是严格教育与温馨启发劝导双管并下。
王船山世代忠于职守,以忠孝传家,祖孙十一代与大明王朝相始终,至王介之、王夫之(船山)兄弟为挽救大明王朝的倾覆而出生入死、奔走呼号,竭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最后事无可为,仍然用自己的笔为民族的复兴而整理总结了一份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确实表现了“到老六经犹未了,及归一点不成灰”(王介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的伟大献身精神与探索精神。
王船山自幼就开始熟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之作,又通晓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从而形成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价值具有一种深深的理解和认同,也就铸就了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无限自信心与对本民族的无限自豪感。
“但我们要知道,这种悲痛不是悲伤、更不是悲哀,而是一种强烈的痛与怒、悲与愤,是一种不甘心、不接受的顽强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他的痛怒、悲愤面前,我们的伤感与同情是完全多余的,更多的将是激起我们紧跟着他的情感和步伐去寻找如此自豪、如此强大、如此优秀的民族国家被颠覆、被灭亡的历史根源!这也是令王船山不能释怀的愤怒之处。”谢芳如是说。
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民生的艰苦、朝廷的腐败、空议的误国
集丧权之悲、君父之仇、民族之恨积于一心的王船山,于是开始“哀其所败,原其所剧”,由此以整整40余年的生命展开了对明王朝之所以覆灭的历史原因的追寻。
而这些导致明朝灭亡的历史根源也就是令王船山至死不能释怀与愤恨之处,这些探索主要集中在他的两部史论著作中《读通鉴论》与《宋论》。
王船山一哀民生之多艰。
在分析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王船山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覆灭首先亡于农民起义,其次才是亡于趁火打劫的满清。农民的生计问题成为王船山关注和关切的中心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意识,使他的思想富含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尽管王夫之对农民革命持敌视的态度,攻击农民为盗贼,但“盗贼”的起义导致明王朝的倾覆,这样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具有忧国情怀知识分子王夫之的神经。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不均”,“不均”是由于“聚”引起的,聚即指豪强地主的兼并,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所以,王船山对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表现出了深刻的同情。在《黄书·大正》里,以一种非常沉痛的笔触描绘了大官僚、大地主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两种生活:一方面,“农夫泞耕,红女寒织,渔凌曾波,猎犯鸷兽,行旅履霜,酸悲乡土,淘金、采珠、罗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而在大地主那一方面则是,“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笑於其上者,密布毕网,巧为射弋,甚或鞭楚斩杀以继其后。”
二愤专制朝廷之腐败。
王船山通过对中国三千年中国政治史的考察,清楚地认识到明王朝的灭亡是三千年专制政治演化的必然结果。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专制集权,废宰相,使内阁、六部皆无实权,由皇帝主宰一切。他对孤秦陋宋的批判就在于其君王施行“以天下私一人”“以一人疑天下”的“私天下”之专制制度,《读通鉴论》“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 ,又岂天下之大公哉!”他认为,家天下的制度导致君王极端自私自利,这是一种注定要排斥好人而任用坏人的制度,最终必然是荼毒生民,危及民族国家安危。
显然,王船山清醒地看到明王朝的制度性腐败是导致明朝灭亡重要根源。所以,他在《读通鉴论》末尾的叙论里这样写道:“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强烈反对和谴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三恨清议之误国。
晚明道学的空疏学风,在文化上导致明王朝积弱积贫,道学先生们满脑子装的是不可违背的祖制和道德的浆糊,在明末兴起了一股清议之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清议派人士,以道德相标榜、排斥社会功利,又常滥用职权、对朝廷政事,乃至军事横加干涉,导致有识有才之士不能被朝廷重用,这批道学家们在政治危机、民族危难时刻,除了空议无能为力。
王船山痛恨这种空疏的学风,所以他主张实学,为社会、百姓造福的实学是王船山终身的追求。再加上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使他比较关注人民经济生活之疾苦,因而导致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反省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
王船山因悲愤而追根溯源,引起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导致在后来40余年的岁月里,他隐姓埋名,解读经典,他的一生,并没有有意识的去创建自己一套学术体系,源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研究中国历代朝廷兴亡的历史,重新解读经典,复兴实学,而且他坚信他写的东西200年后定能被用,更表达了他坚定的文化自信意识。
谢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