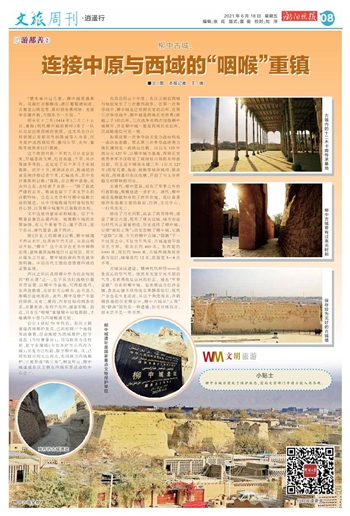■文/图 本报记者 王 靖
“楚水秦川过几重,柳中城里遇春风。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羌酋举首遵声教,万国车书一大同。”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二月二十五日,鲁陈(明代柳中城的称呼)来了一队从北京出使西域的使团,这支风尘仆仆的使团以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人为首,任务是护送西域哈烈、撒马尔罕、火州、鲁陈等地使者回归属地。
这个使团自前一年的九月从北京出发,穿越苍凉戈壁,经历高温、干旱、风沙等诸多考验,足足走了五个多月才来到鲁陈。次年十月,使团返京后,陈诚把沿途见闻详细记录下来,汇编成书,其中有对鲁陈的记载:“鲁陈,古之柳中县地,在火州之东,去哈密千余里……”除了叙述严谨的志书,陈诚也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歌吟咏,这是文史资料对柳中城最生动的描述,从中可窥陈诚当时愉悦放松的心情,以及柳中城塞外江南般的生机。
文中这座诗意浓浓的城池,位于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西面。梳理柳中城的发展脉络,有几个重要节点:建于西汉,显于东汉,唐代置县,盛于明清。
据《历史上的鄯善》记载,柳中城建于西汉末年,但具体年代不详。从东汉明帝开始,“柳中”这个名字在史书中频频出现,意味着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其实从诞生之日起,柳中城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明确:中国历代王朝经营管理西域的重要基地。
西汉之所以选择柳中作为抗击匈奴的“桥头堡”之一,在于其当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以柳中为基地,可西接高昌,东南连敦煌,北穿东天山峡谷,还可进入准噶尔盆地南沿。此外,柳中是物产丰富的绿洲,北有二塘沟、西有吐峪沟两条水系,水量充沛,有利于屯田,储备军粮。因此,只有在“咽喉”重镇柳中站稳脚跟,才能确保中原与西域畅通无阻。
公元1世纪70年代后,东汉王朝重建西域都护及戊、己两校尉三个高级军政建置,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驻守高昌(今吐鲁番市);司马耿恭为戊校尉,驻守金蒲城(今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关宠为己校尉,驻守柳中城。戊、己两校尉分列天山南北,共同拱卫西域都护,三地形成“铁三角”,相互呼应,柳中城遂成东汉王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中心之一。
在其后四五十年里,东汉王朝在西域与匈奴发生了三次激烈战争,在第一次争夺战中,柳中城是己校尉关宠的治所,在第三次争夺战中,柳中城是西域长史班勇(班超之子)的治所。三次战争有两次围绕柳中城展开,并且柳中城一度是西域长史治所,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如果说第一次争夺战关宠力战而殁是一曲浴血悲歌,那么第三次争夺战班勇力挽狂澜则是一曲铁血壮歌。从公元123年到公元127年,以柳中城为基地,西域长史班勇率军不仅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车师前后部,而且还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收复焉耆、龟兹、疏勒等绿洲城邦,驱逐匈奴,西域重归东汉统辖,开创了与父亲班超交相辉映的功业。
至唐代,柳中置县,肩负了军事之外的行政职能,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清代,柳中城还是额敏和卓的王府所在地,是吐鲁番绿洲东部最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时风光无二。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城市命运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历史选择了柳中城,它便“披挂上阵”;历史忽略了柳中城,它就“退隐”江湖。今天的柳中古城,“隐匿”于一片民居之中,不复当年风采。古城遗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1000米,周长约3000米,古城西南角保存最为完好,城墙高约12米,底基宽5—8米不等。
古城虽成遗迹,精神代代相传——在鲁克沁的空气里,依然有关宠宁死不屈的气节,有班勇收复山河的壮志。褪去“军事重镇”色彩的柳中城,也发展成为经济重镇,鲁克沁镇不仅传统瓜果飘香依旧,现代产业也是生龙活虎。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硝烟弥漫的历史舞台中,柳中古城从“主角”到“群演”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对百姓而言,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小贴士
柳中古城目前处于保护状态,需向文管部门申请方能入内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