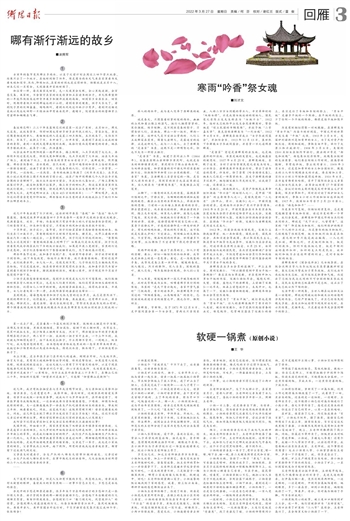■凌拥军
1
壬寅年的春节竟然那么多雨水。以至于之前计划去周边三四个景点玩耍,结果只去了一个地方,其他时间除了拜年,便是因为雨水天气呆在家里看书或看电视和写字。然而,即便如此,在家的时间也是过得好快。转眼就是正月十八,回来已经一月有余,又到要离开家的时候了。
和往常一样,每次离家或回家,先一天夜里会失眠,会心里起波澜,会百感交集。离家时,不舍留守在家的白发母亲和正在读书的孩子,并无限希望新的一年能尽快结束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局面,回到家乡安居乐业。回家时,则期待着快点回到那遥远的小山村,看到母亲还健康,孩子又长大了,看到院子里的炊烟袅袅、鸡鸣狗叫,看到北风吹过竹林沙沙有声,看到河边塘边菜地以及远处田野一片绿油油中有朵朵花开。遇晴日,院前屋后的桃蕾柳芽上有蜜蜂和蝴蝶在飞舞。
2
春运难忘啊!二三十年来最难忘记的是第一次去广东时。正月初六,那天天没亮,我就来等车。邻村四周也有好多好多出外找工的人,背袋扛包,身边还围着相送的亲人。离塘坳远的人是凌晨三四点做饭,五点就来了,生怕坐不到车。车来了,我挤上了车。车开动了,打开车窗,我看到了县道上送我的母亲的身影,看到一夜到天亮帮我缝补衣服、收拾行囊而没有睡觉的母亲,她在用手擦拭泪水。我鼻子一酸,热泪盈眶。
从金溪庙开往衡阳的第一趟早班车,路上畅顺,八点多就到了大元头,再转街车经过莲花大厦、供销大厦和解放路,九点多就到了火车站。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看到南下北上、东去西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成堆,熙熙攘攘。那些卖快餐的、卖水果的、卖汽水的、卖茶叶鸡蛋的和卖车上临时用品的一排排店铺前,站满了穿着不同、行色各异的人们。讨价还价,一手拿货,一手拿钱,一边给钱,一边找零。卖书的地摊上堆满了《列车车次表》、众多武侠小说以及封面上图片肉麻的言情小说。站在广场中间那棵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合围的古老樟树下,抬头往车站四方望去,车流如水人集如云。广场上票贩与旅客讨价声,旅店和录像厅拉客声,路上车子的喇叭声,街边店里录音里传来的流行歌曲,一时好不嘈杂。特别是那汽车客运车拉生意的那个声音:“走啊走啊大元头,走啊走啊四幺五(发往415方向的班车)……”那吆喝声,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那些客运车拉生意的差点就把我拉上了他们不知开往哪里的车上。
3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新词,这些新词中要算“春晚”和“春运”给人印象最深。春晚是改革开放激荡四十多年来每年一度除夕之夜的全国欢庆晚会,充满着喜庆、欢乐、幸福;而春运则只有出外务工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得到:出门时豪情万丈,归来却行囊空空,只有故乡的风和云能为其抚平创伤。
十多年前,孩子还小,春节前,孩子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爸爸妈妈回来。他们坐在门口数日子,算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腊月底,从早上看路口的客运汽车一趟又一趟过去,一直等到天黑,孩子们还不停地问奶奶:“爸爸妈妈怎么还没到家?爸爸妈妈在路上到哪了?”如果我们是白天到家,孩子们是顶着寒风或冷雨在我们下车的地方接我们。如果是半夜三更到家,家里的灯还会是亮的,孩子们在昏暗的灯下昏昏欲睡等我们,见了面就高兴得哭。
那些年春节过后,我和妻子来到广东。电话里听母亲讲:孩子放学回家看不到你俩,放下书包就哭。给他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爸爸妈妈。有时还没开学,我们就要出外,女儿大一点,还能克制不哭。儿子任我们怎么骗他或买玩具给他,可总是没成功,他在母亲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我和妻子在汽车窗口直到看不到孩子和母亲,擦拭满脸的泪水,硬着心离开,孩子则是半个月后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小孩子是很想爸爸妈妈的,想到什么程度是大人们不可想象的。他们孤独的时候在背人的地方哭泣,也是大人们看不到的。他们还有在奶奶生病时的无助和恐惧。记得女儿三四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病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半夜里,女儿打着电筒一步一滑,去找邻居家的婆婆过来帮忙……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母亲和孩子无依无靠的过往岁月,我总是潸然泪下。离别的那种日子,记得最深;来回那条乡路,离我最近;还有那片山水,牵系灵魂;那抔泥土,最是温醇。每次当我转过身,背影消失在我长大的山村时,那个埋着我的先祖又埋着我的胞衣而且我在那里长大的山村就会上到我的心头。
4
第一次去广东,是在番禺一个露天的挖沙场里。低矮的工棚是竹子为架,石棉瓦为顶为墙,里面床铺相连,男女混住。榕树下的工棚四周,水草丛生,芭蕉叶疯狂生长,挖沙场离工棚两百米远。烈日下,那些健壮如牛的男子戴着草帽在挖沙挑沙,两三百斤一担。我挑的一担才百斤左右,一个上午不到,我就被太阳晒得发痧了,接下来就是拉肚子,什么药都不管用。一到晚上,蚊虫叮咬,我又想家想到要哭。后来想起母亲给我包里放的一包家里带来的黄泥,我把它和沙场里的泥以及浸水和起来,待泥沉水清,取水喝下,才渐渐没有拉肚子了。
水土不服,是当年很多出门在外的人的通病。刚刚出外时,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更有用工歧视和暂住证等问题。特别是暂住证。如果没有人送钱来赎,就要送到收容站去。这让无数人心里有了不可磨灭的痛印,以至于现在想起唐代刘皂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心里明白,为什么我在外面奔波三十多年了,在佛山已经二十年,却始终不能够“却望并州是故乡”,不能够“却望佛山是衡阳”!
5
近几年,我才有机会抽空在七月半或清明节回家,为父亲和祖父辈祭拜扫坟。母亲虽在,已是耄耋之年。我很幸福,每次回家,还被浓浓的母爱笼罩着。母亲不让我做一分钱家务事,说我从十七岁开始出外,在外面受苦了。母亲张罗着为我做饭做菜,一边告诫我要为身体健康着想,少喝酒。却因为知道我特别好酒,又一边颤巍巍地拿一些在生产队吃酒席收回来的酒出来,帮我倒上半杯。她看着我吃,问我,这菜咸不咸?这饭煮得硬不硬?母亲还摸着我的头,问我,这几年怎么脱了那么多头发还长了这么多白发?问我,还记不记得父亲过世时那些往事,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家的亲戚族人以及朋友?
我何尝不记得我曾经和父亲生活过来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
民国年间,外祖母六岁,因家里贫寒做了双峰县石牛镇李家的童养媳。父亲是凌家小房的嫡长,从几岁时就开始越金溪过九峰走双峰。当年双峰县城永丰市面上的茡荠,就是我们塘坳当时的特产。我们生产队包括塘坳生产队和父亲一代的人,大多数人都曾挑着茡荠跟父亲走过双峰。那柳暗花明绵延悠长山高水远的路,是我外祖母魂里最亲的娘家路,父亲走了一辈子。我也是小家族里的嫡长,父亲带我北上双峰,南下衡阳,所有的亲戚或远房亲戚家里,都曾留下过我淘气的足迹。
父亲在生时建房子,全生产队的人都来无偿帮忙搬砖递瓦。父亲过世时,全生产队的人都忙里忙外,丧事中做礼生的洪老师,几天后把他当时所得的二十八元钱退到母亲的手里。
……
6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人生却有不散的乡愁。熟悉的土地,母亲站在村头凝望的眼神,桌前床头的家长里短……世事不管怎么变迁,乡愁总是永远的挂念。
余光中的乡愁是邮票是船票,很多年来千万在外的游子的乡愁却只是一张归程火车票。游子拿到车票的那一瞬间会激动不已,会想起下车后眼前的灯火阑珊月影重,匆匆归程夜夜长,会想到家门口“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情景,会想到那人间最温暖的灯火。而每当杨柳青青江水平,春风吹皱塘池水,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园出外远行时,千言万语百感交集只能汇成四个字:依依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