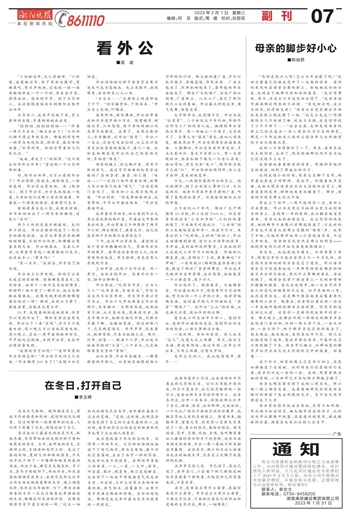■屈 斌
“小孩盼过年,大人望插田。”小时候,我最盼过年,除了有新衣服穿,有糖果吃,有压岁钱收,还能把一挂一挂的鞭炮拆成一个一个的,存在盒子里,慢慢地放,能放到开学。到了正月初二,我还能随爸妈坐车到衡阳去给外公拜年。
正月初二,我很早就起了床,穿上崭新的衣服,等着妈妈喊我出发。
“铛铛铛,铛铛铛铛铛——”伴着一阵片头音乐,“猴王出世了!”小伙伴们顾不得过年的忌讳,都钻到村里唯一的黑白电视机前,排排坐,嬉笑哈哈地看,“水帘洞里,孙悟空带着孩儿们乐无边。”
“斌斌,要走了!”妈妈催。“还不快去给你外公拜年!”旁边的一个小伙伴附和着。
对,给外公拜年,又可以看到外公了!外公很胖,很福态,满脸堆笑,一脸的慈祥。外公家也有电视,演《西游记》。到了外公家,丹丹表妹陪我一起看,不用和你们这群小家伙挤着看。外婆装一个漂亮的团盒,里面有巧克力。
爸妈提着大包小包,我跑在前面。爷爷和奶奶放了一封长长的鞭炮,送我仨“出行”。
两个小时的长途车颠簸后,我们终于到达。外公在楼梯间放了一封长长的鞭炮迎接。我穿过带着浓浓硫磺味的烟雾,扑到外公怀里,仿佛腾云驾雾来到天庭。外公抱着我,坐在火炉旁,从团盒里拿起一块圆圆的巧克力,放在我手心:“晕车吗?”
“有一点点。”我回答,用手指了指电视。
外公马上打开电视,孙悟空正在天庭求助弥勒佛。弥勒佛慈眉善目,笑对访者。我剥下一块巧克力放到嘴里,好甜啊!抬头望了一眼外公,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就像电视里的弥勒佛望着孙悟空一样!顿时,我的头不晕了。颠簸劳累,消散在九霄云外。
10岁,我随着妈妈进城读书,经常可以见到外公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外公立了一条“家规”,学习日不能看电视,周六晚上可以来他家看电视。周六晚上,是我一周中最期盼的时光。早早地吃过晚饭,来到外公家,坐在外公跟前看电视。
“这周的学习如何?”“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得怎样?”外公时不时问上几句话。“作业都得100分了!”我随口如实回答。
外公悄悄地从饼干盒里拿出果丹皮或巧克力塞给我。我立马拨开,放到嘴里,丝丝甜意沁入心田。
“当当当……”五屉柜上的座钟敲了十下。“回家睡觉啦,下周再来。”外公关上电视,叮嘱我。
春寒料峭,微风拂面,外公会带着我和丹丹漫步湘江河边。绿茵铺岸,树枝吐芽,江水悠悠,原汁原味的湘江风光带尽收眼底。走累了,我要求歇会儿;丹丹撒娇,让外公“驼背”。外公一一答应,还会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变出纸盒装的荔枝汁,每人一瓶。我和表妹都感觉外公比自己的爸妈还好,幸福感“爆表”。
回家的路上,经过锅炉房。源源不断的蒸气,通过弯弯曲曲的红色管道输向厂区的食堂、澡堂、幼儿园。“吱吱——”一处阀门向外冒着白烟,就像火车头的蒸汽机在“喘气”。“应该是阀门老化了,值班的小王周日休假去咯。”外公判断。“你先带妹妹回去,我有事啦,中午让外婆送饭来。”外公笑着招呼我。
我牵着丹丹回家,回头看到外公大步流星地奔向锅炉房。外婆送完中餐回来就叹息,外公带着几个师傅修了两多个小时,棉衣都脱了,满身大汗。他已经连续两个月的周日没有休息了。
下午,我从外公家出来。澡堂的大窗户冒出热腾腾的蒸气,里面传出悦耳的歌声。鱼贯进出食堂的工人,端出香喷喷的饭菜。岁月静好,原来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上初中后,我很少去外公家。但一有空,我就去陪外公,陪着外公坐一坐,陪外公聊聊天。
外公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学校生活当然不如家里好,学生伢子要以学习为主。外公十几岁就跟着太外公卖棉纱,养家糊口。天刚麻麻亮,他肩挑百斤担,从文昌出发,花滩迎日出,高真寺喝口水,板桥伙铺吃中饭,杉桥凉亭歇下脚,远眺柘里渡,到达回雁门下,已是晚霞满天。年年岁岁,寒来暑往,酸甜苦辣,尽在石板路上过。购纱、织布、销售……刚满十八岁,外公成为城南年轻的“工匠”,二十出头,已是珠琳巷里坐堂的“掌柜”。
公私合营,外公率先报名。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从老城区相聚到湘江河畔的白沙洲。取土烧砖建厂房,开炉打铁作梭子,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厂房立起来了,织布机响起来了,瀑布般的布匹挂起来了。棉纺厂与轧钢厂、冶金厂隔江相望,厂房林立。八大工厂,奠定了衡阳现代工业的基础。外公每次讲到这里,眉飞色舞,倍感自豪。
大学刚毕业,我思绪不定。外公与我“拉家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外公作为工厂的优秀人选,抽调到市公安局当帮手。有一回碰上一个案子,总是结不了。当事人为“国军”营长,犹如人间蒸发。蛛丝马迹中,外公发现营长祖籍集兵滩。人勤脚忙,外公空余徒步常走访,多次无果而归。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傍晚时分,他在瓜棚下遇见一位老人浇菜。搭讪得知,营长为其“发小”,衡阳保卫战中已成“仁”。外公写好证明材料,老人签字画押,星夜回城复命。
不久,一纸调令落到外公的手上。他怀揣调令,到了公安局人事科门口,又打道回府。他舍不得离开亲手建的厂房,听惯了轰鸣的机器声,还想继续编织五彩的梦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棉纺厂生产规模有10万锭,职工达到7000人。但是食堂管理还是“小米加步枪”,人们的味蕾挑剔了,不再满足吃饱就行。“三班倒”的职工反映饭菜品种单一,味道不可口。本着让职工“吃好饭,上好班”的初心,外公主动请缨到食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半年后,菜的品种花样繁多,上夜班的职工也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外面的人都羡慕,说,在棉纺厂上班,餐餐都吃“十甲碗”。一家央媒以《锅碗瓢盆协奏曲》为题,报道了棉纺厂食堂的事迹。外公也多次被评为省市劳模,这些荣誉,他收集在一个小铁盒里,很少示人。
外公退休了,闲居数月,又返聘食堂。外公最后的日子,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智力如同一个三岁的小孩。他常常喃喃自语,说的最多的几个词语就是“食堂”“棉纺厂”。送外公“上山”的时候,山边满天彩霞,犹如华丽的云锦。
每当我工作生活中不顺心,想到外公,想到外公满脸的笑容,想到外公对生活的坚持,心烦之事烟消云散。
一段时间,寒冷加疫情,家人成为“宅人”,大崽天天上网课。有次,他自言自语:要放寒假啦,快过年啦,过年去外公家,不用上网课,还有压岁钱。
兔年正月初二,我也起得很早,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