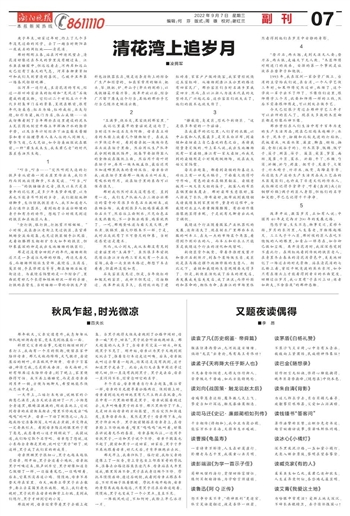■凌拥军
庚子年末,回家过年时,约上了几个多年没见过面的同学,去了一趟当时衡阳县一夜成名的网红地——清花湾。
那时刚刚立春,站在河畔迎风望去,清花湾好像还在冬天的梦里没有醒过来。江水虽在睡朦中,但远远看去,河两岸和远山处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河岸垂柳黄芽细叶和我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已被辛丑年第一缕春风轻轻吹拂。
往河岸一边行走,至清花湾的弯处,经过一排旧砖窑出来的红砖和“见风消”石块建成的建筑物,它们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集市门店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很有年代沧桑感:红石为墙,红砖成柱,石灰勾缝,松杉为梁,板门为店,依山成铺……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在这里建设的泥木土瓦匠因地制宜开路立市挥洒汗水的勤苦辛劳,以及当年计划经济下油盐柴米酱醋茶和昔日接踵摩肩人来人往的人间烟火。繁华飞逝,已无见证,如今沧桑斑驳就在眼前,一种“君生我未生,我来君已老”的时代落差感油然生起。
1
“叮当,叮当……”突然听到久违的打铁声音从前面一间石屋里传出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不再笑谈。“叮当,叮当……”的铁锤锤击之音,很久以来只是在童年的记忆里,是多少年来梦牵魂萦、以为再也不能亲耳听到的乡音。我们轻轻地挪动脚步,生怕惊扰铁匠老人。我不知道老人在打造什么器具,看到他老当益壮矫健的身子和有力的动作,想起了小时候见到过的铁匠和其他匠人来。
“金打铁,银打铁,打把剪刀嫁姐姐。”小时候,我在渣江老街上见过铁匠,在官埠枫坳金溪庙赶集,也见过铁匠铺手拉风箱、光着粗胳膊生相粗犷力大如牛的铁匠,但印象最深的却是我出生地塘坳的铁匠们。
那是还没有分田到户的年代,塘坳新街还只是一条通往九峰的砂路,两边无房无店,而塘坳供销社生资部、裁缝店、豆腐店、篾匠铺、手表修理店等等,都在塘坳石板老街这边。与裁缝店隔壁的是一个综合厂,里面就有好几个长得和绿林好汉一样的杀猪、打铁的在营生。当时塘坳一带的冷铁生产资料包括铁器农具,便是这条老街上的综合厂生产和经营的,如农家常用的锄头、耙头、犁、铁耙、铲、开山子(斧头的别称),以及铁锤菜刀柴刀等。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厂只留下屠夫这个行当,其他的那些手艺行当已随历史烟消云散。
2
“王满爹,烧石灰,果窑烧到那窑里。”
我记忆里最早的童谣就是这句了,当时还不知道石灰为何物。母亲在土砖房的木楼上放着几个储物坛子,在我五六岁快过年时,看到母亲把一块块白色石头放在坛子里面,然后用从生产队年底分到的报纸隔开,把春节要招待客人的食物放在报纸上面,然后用干荷叶封在坛子口,再用一块木板盖住,最后还用不知道哪里找来的青砖压住。母亲告诉我:放在坛子里面那一块块石头叫石灰,有吸水的作用,放在坛子里的东西可以保存很久。
那时我仍然对石灰没有感觉。直到有一次,我们生产队派人去三湖公社那边的雷寺岭买很多白色石头挑回来,放在晒谷场。我看到很多人把鸡蛋藏在那白石头下,然后往上面倒水,只见白色石头发热散化,不一会取出鸡蛋,鸡蛋就熟了。一吃,那鸡蛋味道与柴火炭火煨、开水煮、铁锅煎、猛火炒根本不一样。于是,我对石灰就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还感觉这是魔术。
然而,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童谣里的“王满爹”。虽然很多年前桃花堰往渣江方向两三百米处有一个石灰窑场,我每一次坐班车路过,都想下车去看看,但最终没能如愿。
石灰窑匠没见过,但是,当年烧红砖和做瓦的窑匠,我却不但见过,还接触过。改革开放没多久,农村就兴起了建红砖房。家家户户做砖烧窑,我家曾经就烧过五窑红砖。从塘坳到渣江五公里的路边有四家瓦厂,那些窑匠们当时名满乡里威震四方。然而,在以江浙人为技术代表的大型砖瓦厂兴起之后,这些窑匠们就失业了,他们的技术也就失传了。
3
“骚裁缝,臭皮匠,怼死个剃佬匠。”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谣语。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人们穿的衣服,以中山装和人民装最多,是买来白洋布,到染铺和染坊染上自己喜欢的色之后,再请裁缝量身定做的。听上辈人说,我出生地塘坳就有一家染铺,渣江有一家大染坊,而我见到的染铺则是小时候赶枫坳场,就在我大姑父家隔壁。
每次去赶集,都看到染铺的街基边土砖灶上有一口龙头锅子,下面柴火烧得呼呼作响,有色的染水在锅里翻滚。染铺老板用一双又长又粗的筷子,把客人的布匹在锅里翻来覆去。那时染布生意很好,客人排成了长队。待布染好,把布放到裁缝铺或请裁缝来到家里制作,量身的过程中,女裁缝对衣主人要量胸围腰围,有些动作像搂像抱显得亲昵,于是就有无聊者出此戏言调侃。
裁缝这个行业随着服装产业机器化的发展,逐渐消失了。现在制衣厂里那些车衣服的叫车工。在大一点的市场某个角落,看得到个别补衣的人,而车工和补衣工只能算是裁缝这个行业的演化和残留吧。
剃佬匠背个板凳,带着手推理发剪刀和磨刀石剃须刀,到各个屋场做生意。皮匠就是在马路边摆个地摊修鞋的生意人。相比之下,染铺和裁缝的生意规模要大得多了。但是,剃佬匠演化成了后来的理发店,再发展成美容美发店,成了洪流;而修补鞋的和算命的,相依为命,在渣江的市场里依然看得到他们在岁月中安静的身影。
4
“磨刀石,两头翘,走到天涯无人要;磨刀石,两头低,走遍天下无人欺。”木匠师傅对刚进门的徒弟,安排的第一个事就是让徒弟去磨斧子和铇铁。
1993年,我在深圳一家合资厂做工。台湾的主管给我们说,在台湾,一个人学艺快三年时,如果师傅突然过世,麻烦了,这个学徒一辈子出不了师了。不像你们这里,跟师傅学三个月,就要和师傅一样的工钱,然后不需要跟师傅走,可以到处去做手艺。
今天已经很少有过去那种学艺三年才可以出师的匠人了,现在大多数的木匠砌匠都是形像而神不像。
那些曾经在人们生活中有千百年历史的生产生活用品,现在已经越来越稀少:水车子、风车子、扮桶和比较先进的打稻机。花板梁床、双层水架、澡盆、脚盘、橱柜、抽箱、仓柜(放谷子的)。竹木蒸筝、饭桶、饭宁子、筷子、涮箕、筛子。簸箕、箢箕、箩筐、扁坦、篾簟、斗苙、蓑衣。淤船、牛丫、水桶、勺筒、淤桶、淤勺、潲盘。把弯子、炭盘子、火架子、竹木椅子、竹凉床、板凳、马蹄桌等等。而还能生产这些生产生活用品或工艺品的木匠篾匠们,也许成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人。我依稀还记得手拿斧子、哼着《盘洞》或《打铜锣补锅》调子的匠人身影,但他们的名字和笑脸,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
5
改革开放,激荡岁月,正如有人说:中国用40年走完西方200年的发展之路。
悠悠宇宙,生生不息,物事变迁,星移斗转,岁月的长河里,人生易老,万物缘起缘灭。三工九子十八匠,那时候的匠人在吃不饱饭的人的眼里,如青山一样存在,如今却已微如尘埃。离开清花湾时,我深深感觉到不虚此行:在网红地看到传统的铁匠老人,在身置冬去春来的清花湾景色中,美美地回忆了一场过去的时光景物。站在清花湾的七孔桥上看,曾经千帆竞渡的蒸水长河,如今只有在堰头上才能看得到昔日的水面宽度。回顾过往岁月,我心里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那种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