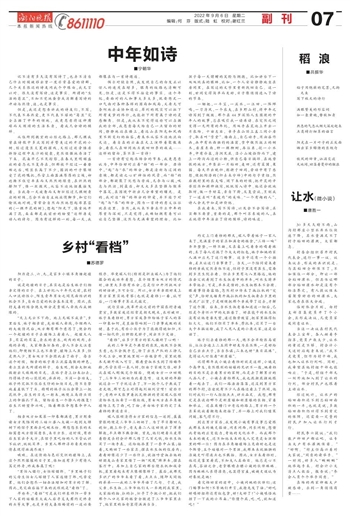■宁朝华
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写诗了,也弄不清自己什么时候被移出曾一度非常喜爱的诗群,几个关系很近的诗友问我个中缘由,我无言以对。很久没有写诗,这是事实。所谓的“生活的苟且”,不知不觉地蚕食或消解着写诗的冲动与热情,这,也是事实。
但是,我还是想告诉我的诗友们,不写,不代表不再热爱,更不代表不堪的“苟且”完全占据了中年的领地,我更愿意将这种庸碌而又烦琐的生活本身,看成几分诗的模样。
从住所到教室的必经之路上,那几棵我曾在诗歌中多次写到并赞美过的开花的小树,经过漫长炎夏的摧残,又经过近旁楼房拆除过程中灰沙的侵袭,竟然倔强地存活了下来。花朵早已不见踪影,在春天里明媚盛放的姿态也不复存在,但那枝干经过一番磨砺之后,明显长高了不少,圆润的叶子像领受了花的嘱托,尽管上面落满厚厚的尘埃,却遮掩不住它率真而又热烈的绿意,在炽热的骄阳下,借一丝微风,从容不迫地招展摇曳着。当我每一天疲惫而又匆忙经过几棵树身边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和它们愉悦地对视,常常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想起“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这样凄美动人的诗句。因为有这样的一刻,每一天,我都像在与一首诗邂逅。
偶尔对镜自照,我发现自己的白发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多,眼角的纹路也清晰可见,但是,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这个年纪,要面对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既要憋足一口气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局和残局,又要无可奈何地去妥协和退让,犀利的现实可以扯下所有美梦的纬纱,也能折下所有属于诗的灵感触角。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些可以占据我的全部,我愿意每天给自己一点留白的时间,静静地站在楼上,看远山在阳光和风雨里不断变幻的妆容,看耒水从容不迫地流向天边,看自在的云朵在天上演绎着聚散离合,看农人在田间地头载回四季的收成……这样的留白,算不算一首诗?
一首诗有它起承转合的节奏,我更愿意认为,中年恰好对应着“转”的一部分。唐诗中,“起”与“承”的部分,都是清新与辽阔的意境,都是读之心旷神怡的风景,而“转”的部分,都凝聚了忧愁与苦痛,无奈与心酸,叹息与热泪,到最后,却又大多在坚强与傲岸中落笔,在困境中折出几分希望的曙光。是的,我对这“转”的部分的钟爱,并不逊于对“起”与“承”的部分,因为一首诗的意义往往就在这里。当然,我从来不奢求什么中年的厚重与深刻,只是觉得,我确切拥有着可以让自己坚强、淡然与充满希望的理由。比如孩子每一天馈赠的笑脸与拥抱,比如讲台下一双双纯真的眼眸,比如,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在写过的文字里重新找回自己。这一刻,世间变得简单而美好,日子像悄悄进入了诗的节奏。
一锄耙,一斗笠,一溪水,一汪田,一阵蝉鸣,一习清风,一个农夫,在乡野山村,将中年之诗写到了极致。那个在44岁深陷人生困境的中年人的故事,总在吸引我一读再读。在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的年纪,用双手在荒地上开出一片农场,十亩左右,亲手在山顶上盖三间小房子,取名叫“雪堂”。墙面上,自己动手,用油漆作画,画中有水面独钓的渔翁,雪中傲然挺立的树木,房屋东面,种一棵柳树,再往东,挖一小水井,中有冷泉,清洌见底。沿小山坡拾阶而下,建上一跨沟而过的小桥,供自己每日徜徉。在地势低的地方,开垦出一片稻田、麦田,还有菜圃、果园。每天早出晚归,躬耕于田间,劳动中有了感想,便把陶潜的《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重组,然后教村里的农夫唱。闲下来的时候,把开荒的辛苦经历和耕种诀窍,统统写入诗中。他还会就地取材,做一手好菜,亲自下厨,反复尝试,烹制成了一道名叫“东坡肉”的美味。“一个有趣的人”,诗人余光中如是评价他。
在我看来,写不写诗,以及会不会写诗,其实都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个叫苏东坡的人,真正地将中年活出了诗的模样,诗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