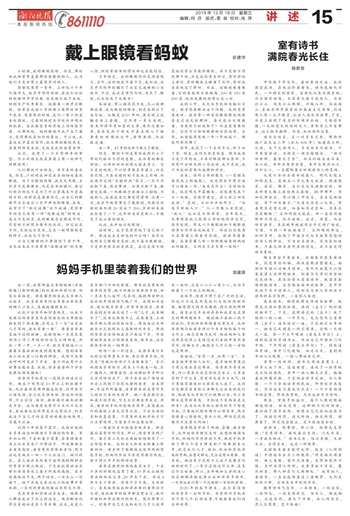中华数千年文化,盛世崇尚文治,乱世推崇武功。在统治阶层看来,读书能教化万民,一个稳定的国家,需要礼仪来巩固皇权;而当国家动荡,又需要无数习武的人,为其打江山。及至江山稳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皇权忌惮手握重兵功高盖主之英雄,怕这帮人有一天不服管,拉出人马反水滋事,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杯酒弃兵权、火烧将军楼,一大批毫无战功的文人,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站上权力巅峰。历史,如此循环往复。
读书与功名,是一对孪生兄弟。隋炀帝杨广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建进士科,之后,天下之读书人,多为功名而读书,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一朝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功名利禄滚滚而来。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之心,一直攫取着古时候读书人的灵魂。
也有不为功名读书的高人。明代大儒王阳明先生,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这位老先生满腹经纶,却在科考之路上连续两次落榜,28岁那年,参加礼部会试,得以赐二甲进士,直至龙场悟道,写下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能文能武,却一直在仕途郁郁不得志,经历被贬,追杀,闲置,而后辞官讲学,再在晚年被启用去平定两广叛乱,可惜,不到一年就病逝了。王阳明的命运,坎坷多舛,浓缩了中国古代大多数有思想的读书人的命运。不为功名读书,是为良知读书,只要忘掉自身外在的得失,是不会觉得读书累的。
隋末李密牛角挂书,汉朝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西汉匡衡凿壁偷光,南朝时齐国江泌映月读书,晋代车胤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孙康冬天常利用雪的反光读书,东汉孙晋头悬梁读书、战国苏秦锥刺股读书。这些勤奋读书的故事,是中华民族千百万读书人,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的真实写照,一直催人奋进。
夜来读书,偶得钱穆大师读书故事:钱穆先生读私塾的时候,读到《孟子》的时候就辍学了,于是,没有读完的《孟子》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一年冬天,先生忽然立意要将《孟子》通体读过一遍,于是拣定大年初一,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空屋里,自限一天读完一篇。第一个上午便读《梁惠王章句》上,读到能通体背诵为止。然后自己开锁出门吃午饭。下午则读《梁惠王章句》下,到能通体背诵,再开门吃晚饭。如是七天,直到新年初七之晚餐,一段心事始告完毕。
曾有一段时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许多人放下书,追逐欲望,造就了一批有钱没文化的国民。其中一些人胸无点墨,偏偏喜欢附庸风雅,于是闹出许多笑话,令人捧腹。一个不崇尚读书的民族,即便经济再发达,恐怕也是尔虞我诈丛生!一个不崇尚读书的富商,即便再有钱,恐怕也会守不住吧。
现在,智能手机盛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阅读。但我觉得,这种碎片化的阅读,看似读了很多东西,好像自己已经知道很多了,但读无所思,读无所悟,读无所得,刷屏罢了,终究浅尝辄止,是不能读进去的。
读好书,明事理,修心性。钱穆先生有联:“室有诗书,满院春光长住;门无车马,一湾溪水细流。”读书之乐,恬淡素雅,无欲无求,自得其乐,也是一种境界。
王国维是著名国学大师,他在《人间词话》中将读书分为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等俗人,喜读书,一直未能悟透这三重境界,大约是修炼不够,还须在书中继续淬炼。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一杯清茶,一抹阳光,一段美好时光。书与人,物我相忘,沉迷其间,看天下万物,品人间苦乐,思人生因果,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