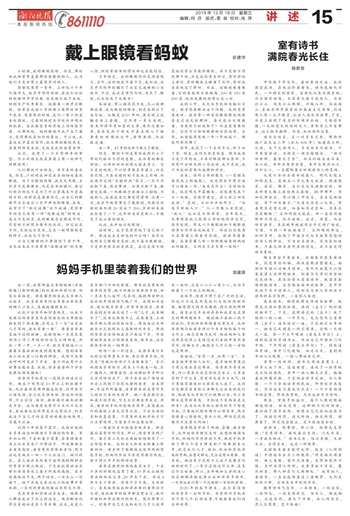小时候,我的眼睛很好。但是,那时的我却常常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认为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
隔壁院里有一青年,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生,数学学得特别好,在我们公社的秋塘坪中学任教。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回到生产队里务农。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经常在我读小学的静尔庵附近田里干农活。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爱来校园玩,总看到他趁来学校水井喝水的机会,在我教室里的黑板上演练数学题。从那时起,他的眼镜对我产生了魔力,觉得那就是知识的象征。可以说,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与那副眼镜有关,在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从此,我有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梦想:什么时候也能在鼻梁上架一副神气的眼镜呢?
人们都说叶公好龙,并非真的喜欢龙。但是,少时的我却是真真切切地喜欢眼镜。为了与眼镜结缘,我天天用眼,当然并不是看课本,而是杂书和报刊。看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崇高或不崇高的目的,纯粹就是看看而已,让自己的眼睛早日去适应心目中神圣的眼镜。后来,我学习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觉得昔年的自己很有一种“毁眼适镜”的味道。真正可笑的是,我的眼睛老是跟我作对,尽管时不时因为看书而流泪,但它就是不坏,无论远还是近,总是一副明察秋毫的样子,让我无可奈何。
与自己眼睛的斗争持续了若干年,当然后来我不再带有“毁眼适镜”的恶魔心理,但经常读书的惯性却也未能刹住。
不幸的是,我的眼睛仍然是洞若观火。当然,这时的我不喜不悲,我知道,这是岁月的年轮圈定了我毫无涟漪的心态使然。不过,我还是喟然而叹:再见了,眼镜,此生你我了无缘分!
俗话说,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我与眼镜的缘分,倒是真的应了这句话。大概是2010年吧,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报,突然有一重大发现,原来印得字黑如墨的文章,居然淡雅如素,某些笔画少的文字甚至隐入了暗黄色的新闻纸之中,若隐若现,与我捉迷藏。
这一年,47岁的我终于戴上了眼镜。
但是,眼镜不但没有给我弥补上少年时代盼而不得的遗憾,反而有的都是烦恼,必须时时刻刻将之揣在身上。它不是近视镜,可以经常架在鼻梁上,而是老花镜,只在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而我要用它的“关键时刻”很多,一旦不用就取下来,很是繁琐。如果不取下来,戴着它走路,一双眼珠子就要往上翻起,不说别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还有一次,我在外面有事忘了戴眼镜,用微信付款时居然将20写成了200,幸好回来后我检查了一下,也幸好店家是熟人,才避免了没必要的损失。
从此,我开始讨厌眼镜。
这时候,我才觉得背叛了自己的少年。难道我真是好龙的叶公吗?虽然从发现自己眼睛老花时,就不喜欢戴眼镜,可是毕竟现实就是现实,我还是很不情愿地经常去买廉价眼镜,并不是舍不得花那个钱,而是我经常弄坏它。有时掉地上摔烂,有时躺床上睡着了压坏,有时放在某地忘了带回。而且,这眼镜戴着戴着,它的度数便水涨船高,100度150度200度,纵深发展的趋势让我心惊。
我的工作,天天与手机和电脑打交道,便寻思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愿景很美好:能否有一种老花眼镜像近视镜甚至是通光镜那样,每天能全天候戴着,勿需时不时地取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抑制眼睛的老花趋势,当然,如若能将度数一年一年地减少,那就阿弥陀佛了。
前年,我花了一千五百多元,终于如了愿。但是,我仍无丝毫欣喜。因为我再不是少年的我,不再对眼镜神往崇拜,不再有叶公好龙的心态波动,我只是我,我只为我的需要而选择和付出。
后来,读何立伟的散文《一觉醒来看见地上的拖鞋》,我觉得其中有句话可以借来一用:“未来是什么?具体的未来,就是明天早晨醒来,还能看见床下头一双鞋,还能穿着它,在人世上四处走动。”是的,正如辛弃疾所言:“白发多时故人少。”人一旦戴上老花镜,“故人”也必是日渐凋零。去年某天,无事便在纸上默写小学时的同学名字,居然发现,有五六个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男女同学永远地走了。而我们还能每天在鼻梁上架着老花镜,读读书看看报,或者是像儿时一样瞧瞧墙角的蚂蚁如何搬家,又何尝不是幸事一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