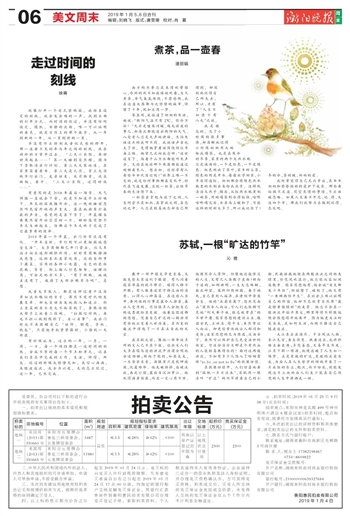展开一部中国文学史长卷,无数先哲大家遂列于眼前。有人闪着儒家毕露的战斗锋芒,耀得人睁不开眼;有人散着道家宁静淡泊的清香,沁得人心神荡漾。在这些人当中,要问谁的行事是最令人推崇,最让人受用的,恐怕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苏东坡。他兼容儒道佛的思想,凭着自己旷达的心胸游刃有余地应变着人世沧桑,在历史的激流中撑起了一片真正自我的天空。
在苏轼之前,像他一样命运多舛的文人已不在少数。这些文人们大多在儒与道的洪流中泾渭分明地分道扬镳;倾向于儒的,如屈大夫,一生苦苦求索,满眼里只是乾坤疮痍,忧虞难毕。他先被排挤,后被流放,再是亡国,最后自沉汨罗江。他死得满身伤痕,而且一定心有不甘。他固然令人景仰,但像他这般惨淡的人生,又有几人再敢于直面?倾向于道的,如陶渊明,一生大志难酬,数次辞官,最终归隐田园,妻子病死,自己靠别人接济,在潦倒中苦度余生。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令人向往,可人们也依稀可见他“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不甘平庸。儒家思想的建功立业、报国安民、立功名、慰平生,虽然常让人向往,却更经常性地让人郁闷和受伤;道家思想的无为隐逸、淡泊安宁,虽然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浊世的伤害,可这份清冷又哪是个有热血的人能轻易熬得住的?面对这两股洪流,不知有多少人陷入了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犹豫彷徨。
在犹豫彷徨中,人们惊喜地看到“孤帆一片日边来”,苏轼用一根名叫“旷达”的竹竿撑着自己的小船,优哉游哉地驶在两股洪流之间的夹缝里,任凭风吹浪打,他总能从容似闲庭散步。儒家思想他有,他会说“老夫聊发少年狂”,但碰壁了、被贬了,他又有“一衰烟雨任平生”。在社会上难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却不忘欣赏自然界“最是橙黄桔绿时”的美景。他总不会在一股洪流中钻牛角尖,哪里待得不舒服他便会很想得开地离开。因为他更关注的是自我,是如何生活,而绝不强迫自己随波逐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无穷,吾生须臾。执着追求,也许终难名垂史册;多愁善感,又易早生华发。江月下斟一樽酒,他便道破了人生如一场梦。正是东坡的旷达,东坡的关爱自我,为后人在人生哲学的领域开垦了一片永恒的乐土,肥沃,而不纷乱,使能发现这片土地的后人们至少能在自己须臾的人生中潇洒走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