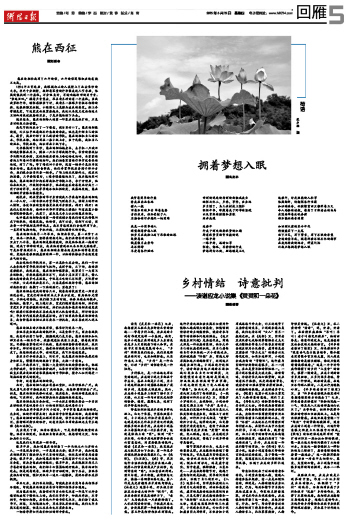乡村很大,是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题材。应龙的小说大多都在千字左右,基本上都是小小说,用小小说这样极短小的篇幅来概括广袤的乡村,是有很大难度的。然而,应龙的小说基本上做到了缩千里于尺幅,而且有一种与田园风光相符的恬静、悠闲、蕴籍之美,达到了近乎诗意地批判。
诗意批判体现在矛盾的多样处理上。比之于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小小说不允许把矛盾复杂化,也就是说不允许在主矛盾之外设敷设很多的次要矛盾。应龙的小说基本上每篇都只有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结构上的“简”。做到“简”并不难,而将矛盾处理得符合体裁而富有意味,则需要很高的技巧。通读《灵灵和一朵花》,我发现应龙大抵采用如下办法:第一种是矛盾预先解决余波荡漾不已。如《关怀》、《七里庵》、《病》等,采用这种方法往往能更充分表现人物,使得人们审美的焦点产生转移,达到诗意的“隐”。正如金圣叹所说:前文匆遽,后文舒缓,疾雷激电之后,偏接一番烟霏云卷之态。第二种是先充分铺陈后矛盾迅即解决。《杜老大》这篇小说,开头极力渲染黑社会老大的种种“烂行”,最后在杀猪匠明晃晃的醉刀下,“老大”立马被当成一只瘟猪给捅了。人们在阅读的时候,于极度厌恶之后,会突然获得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第三种是相伴相生水到渠成。这种矛盾处理办法虽然不如前两种能给人造成较大的悬念,但能够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使读者参与情节的安排和问题的解决。《这只鸡有生理问题》是典型代表。阉鸡大师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他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在自己崭新的自行车不断被一只小母鸡攻击,最终被鸡粪“污损”后,阉鸡大师居然把这只母鸡给阉了,还说这只鸡有生理问题。小说在进行过程中,读者都会为这只鸡的不断挑战而发出来自内心的微笑,大家慢慢明白有问题的是阉鸡大师及促成其形成的背后事物,小说也顺利完成了发人深思的“影射”。除此之外,应龙还在矛盾处理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段爱情的四种死亡方式》里,围绕罗小罗的死亡,众说纷纭,小说始终没有交待真正的“矛盾”是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四种观点均不是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出发,都抹上了功利色彩,四种死亡方式都是 “爱情”的死亡方式。这样的处理,比交待清楚矛盾更有意义,有利于在极短的篇幅内充分呈现“爱情”的环境,发人深思。总之,应龙通过多变的矛盾处理,营造了小说多样的审美愉悦。
情节紧随矛盾而来,也是小说的重要支撑。应龙很好地控制了情节的运用。首先是虚与实的有机交融。金圣叹在论及小说的情节时说:须知文到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正复不定……应龙在安排情节时,超越了虚实相间就是机械、简单的间隔的层次,体现了自己的匠心。《八月》这篇小说,实写庚和庚的女人在明月之夜的劳动、对话和恩爱嬉戏,虚写的是庚的违法犯罪刚刚出狱,只是交待了庚光亮的脑袋和一句“我好悔”以及女人的几句劝慰之语。没有这隐隐约约的几句虚写,小说就会不存在。而如果小说把虚当实大写特写,不仅会把小说写成思想斗争大会,而且还违背了夫妻特有的关系,小说就会毫无美感,我们也看不到“女人”明月一般的光辉。在《关怀》里,实写老黑在风雪之夜给因孽情抛弃丈夫又被无情抛弃带着儿子孤苦生活的前妻送生活用品及物资,虚写的是老黑前妻对“苦力丈夫”的嫌弃以及婚变过程,如果不这样写,小说就会成为新的“寻情记”。这种虚与实的巧妙安排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其次是紧与松的辩证统一。一篇小说不能老是大波大浪,海啸雷鸣,令读者长久地心弦紧绷,还应该有风平浪静、风光旖旎的景色,使读者的心弦在紧绷后得到松弛,以迎接新的浪潮。应龙深谙其中之妙。《较量》这篇小说三松三紧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化了主题。《村长之死》的松紧安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村长设局要阉猪匠阉猪、村长要挟阉猪匠赔钱并没收工具、为给李四家阉猪阉猪匠两次到村长家借自己被没收的工具、村长“不借”工具还不允许阉猪匠到邻村借工具、在抢夺工具中无意致死村长,小说一路写来,跌宕有致,加上小说中的语带双关和戏谑式的轻描淡写,使我们看到了“冷峻的沉痛”。另外,应龙还有一种淡化情节的写法,如《秋唱》等几篇小说。这些小说有着散文诗的语言和意识流的痕迹,善于营造一种氛围,隐隐有沈从文和汪增祺的美学风格,体现了应龙的多样化追求。
诗意批判还在于刻画的精省和传神。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有其基本规律,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人物的倾向应当从语言、行为、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作家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应龙很好地掌握了这一要决,在运用语言、行为、细节、场面等要素刻画人物时做到了精省和传神。应龙在人物语言上,往往寥寥数语,人物即活灵活现。《杜老大》里,杜二甫吩咐“岳母”,说,开房,开房了。在杀猪匠威胁他“再叫!再叫!老子叫你变死猪后”,他的回答是:你有种就过来。这是典型的黑社会流氓无赖的语言。《许多的老婆回了娘家》里,村长教训许多“没有杀气怎么能当领导,像个糯米团团像个宫里的太监,别人屙尿朝你射的是满头满眼,你还只能说谢谢浇灌栽培。”这是一个平时作威作福惯了的乡村“土皇帝”的语言。值得一提的是,应龙小说的语言多用短语,且多间隔多省略,营造了一种活泼、跳跃的美感,在这里不作深入探讨。二是以行为透视心理。《许多的老婆回了娘家》里,当“许多的老婆披头散发嚎叫着朝着娘家的方向驶去了”之后,村长老婆在睡觉时“轻松地鼓起一口气,将离床八尺远的那盏油灯吹灭了。”虽带夸张,但那种获得平衡后的畸形心里跃然纸上。三是场面渲染情感。在这里我着重提一下“场面”中的景物环境描写,因为应龙的小说有一种诗意,而这种诗意很大程度上又依赖它而形成。《秋唱》的临近结尾这样写到“空旷的田野里一段如泣如诉的歌谣,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撒向了天地的四方。不远处一棵苦楝树上一群打盹的鸟儿惊醒了,扇动着惊恐的翅膀箭一般逃去。”这一段描写很好地渲染出一对老年夫妇伤心、落寞、失望的心情。在小说集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场面描写,我不一一举例。
在雁城文坛,应龙应该是小说界的中坚。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报人,他保持了“乡村”的纯朴,不断地写出属于乡村和城市“反射”乡村的作品,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我相信应龙能够不断超越自身,超越已有的作品,用纯朴的乡村情结和在城市生活获得的深刻感悟,写出属于时代的大作。
■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