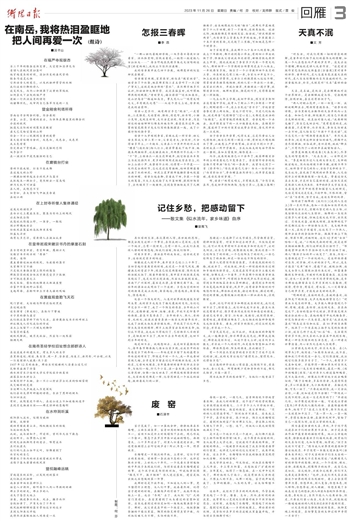■李 昂
“一颗心融化着酸甜苦辣,一双手每日每夜忙活着家。泪水肚里咽,零钱省着花,一把情一把爱把儿女拉扯大……”每当哼起农民歌手朱之文演唱的这首《疼爱妈妈》,我就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的母亲离开我已四十余载,她那慈祥的仪容却犹在眼前。
母亲娘家姓魏,家里很穷,租住在“魏家祖堂”。祖堂办了个私塾,她在那里隔三差五旁听了一点《增广贤文》,这就是她全部的“墨水”。虽然那字她多不认识,但话语却大都背得。我还在摇篮时,就听惯她那熟稔的眠歌:“昔时贤文,诲汝谆谆”“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就是我的启蒙师。
母亲心灵手巧。她有两宗手艺“绝活”,一是剪纸,二是绣花。无论剪的、绣的,荷花呀,牡丹呀,小猫小兔呀,龙凤呈祥呀,无不活灵活现。邻里乡亲,乃至好远的姑姑婶婶们都来拜她为师。每逢农历过年,她剪的窗花跟秀才先生们写的春联摆在一起,成了小镇圩场的抢手货。
母亲十七岁嫁到李家,家境也是一样穷苦。祖父母生养我父亲三男一女,父亲是老大,分伙时,只分得亩多旱土,一斗糙米。父亲在二十里开外的竹山湾“槽屋”(造纸坊)给人打工,母亲带着我下地干活。她抱来两捆稻草,让我睡在地头,用两根竹竿扎成一个“十”字,上面再扎一床豆花布被单,把它拴在水车架上为我遮挡烈日。更多的时候则是把我背在背上,比如上山掐小笋、釆蘑菇什么的。记得有一个早晨——大约是谷雨时节,总之是还没有插秧,稻田里裸露着汪满了水的田泥,田泥上星罗棋布般躺卧着吮饮露水的田螺。母亲打起赤脚,背着我下田,手提一个偌大的篾篓,不大工夫就捡了大半篓田螺。提到圩场卖了,去肉铺买了一块猪肉,还到杂货摊给我买了几颗糖珠子。后来她跟我们兄妹“翻古”,说那天早晨她竟捡了十八斤田螺,称了一斤猪肉,还剩角把钱。说话之际,她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俗话说,“好汉难提四两重”,而母亲背上背着大半岁的娃娃,手里提着二十来斤重的东西,足足赶了三里路,可知她是怎样一个好劳力。
由于家境贫寒,在我那个八十来口人的屋场,跟我上下年龄的,都只读到高小毕业,有的初小毕业就辍了学。惟独我父母说我书还读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中学,因此我就成了李家多少代第一个有文化的人。那时初中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是五十八块五,一年就要百多块,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四个来月的工资。而其时我已有三妹一弟,全家七口开支不小,加上我的求学费用,父亲打工的微薄收入远远不够,得靠母亲养猪养鸡相助。别的人家一年出栏一头猪,我家出栏两头。单说打猪草、煮猪潲这一揽子事,就够母亲忙的。她那双剪纸、绣花的巧手,变得像桑树皮一样粗糙。
一九五七年上学期,我初中毕业,因为家乡衡阳县没有高中学校,我考入了衡山二中(今衡东一中前身)。刚刚读得一半,逢上全民过“苦日子”。学校食堂每餐定量三两米饭,菜也少得可怜,不是几坨红南瓜,就是两箸“无缝钢管”(空心菜),又都是没放油的“红锅菜”,我常常饿得两眼发黑。母亲发明一个办法,把牙缝里省下的一点口粮磨成米粉,在锅里炒熟,装进封了口的竹筒里让我带去学校,每天用开水泡一点充饥。
由于母亲长年劳累,吃得又差,总是尽量让儿女吃得饱些,她自己则有一顿没一顿,有时就只喝洗锅水了事,以致患上严重的胃病,去世还不到六十岁。其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当我从妹夫的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真如五雷轰顶,悔恨莫名……
而今,我离别故居已六十余年了,故居那栋百余年的土砖老屋也已不复存在了,身边留作母亲的纪念物只有布满“筛孔”的一条床单。我曾为之写了一首《垫单吟》:“筛孔笤筋已几分?白头一似卧松云(“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诗句)。此单曾是摇篮被,慈母乳香时梦闻。”
啊,母亲!“鸦有反哺义,羊有跪乳恩。”今您言犹在耳,您我却早阴阳两隔。悠悠寸草心,怎报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