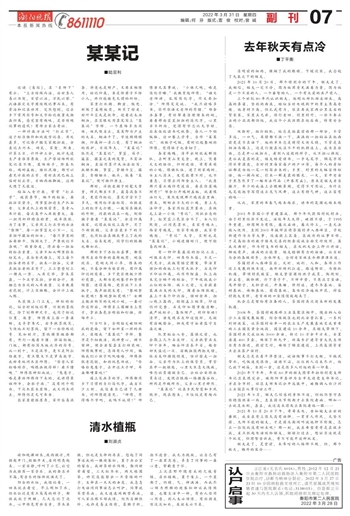■陆亚利
近读《易经》,其“系辞下”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此语推定文字因结绳记事而来,有资治和记录功用。突然想到,过去乡下常用符号和文字标记数量或物品归属,感觉蛮有趣味,是否结绳记事的遗风?有待方家去考证。
一种计数方法叫“打正字”,适于标准物件和纯数字记录。用处甚多,可记每户缴交家肥担数,分类记点竹木、砖瓦、家禽、鲜鱼,计算工日、计件评工分,统计先进生产者推荐票数。生产劳动场所纸笔记录不便,屋场垛子,阶基木柱,鸡埘盖板,猪栏泥墙,都可以看见计数的正字。有时在泥巴地上临时划正字,日晒雨淋脚踩,过两天便了无痕迹。
稻谷入仓计数,常常“打正字”。收获季节,晒干的稻谷,要挑壮实劳力,用箩筐担进生产队谷仓。父亲是队上的保管员,负责入库计数。每次集中入库数量大,每一担用杆秤精准称重,效率很低。为了省事,父亲用上打正字的办法“偷懒”。每一担箩筐大小不一,父亲招呼撮谷的妇女:“每只箩里的谷要擀平,隔阂大了,产量就记不准哦。”称重除皮,得出每一担谷的标准重量。父亲不知从哪里捡来粉笔头,在谷仓泥墙上,写上每个担谷者的名字。挑来一担谷,父亲在挑谷者的名字下,工工整整划上一横或一竖。入库完毕,拿来算盘,一个正字五担,分别合计,再捆总为当次的入库数量。父亲戴着老花镜,计上实物账,会计计上收入账。
木匠做上门工夫,神秘的标记,似古时刻纹记事。竹制的墨线笔,除了划榫卯尺寸,也用于标记位置、数量。师傅肩上搭一条澡帕,左手拿角尺,右手执墨线笔,飞快地点划墨线,留下一些特殊记号。笔如刻刀,墨线横竖撇捺都有,外行一般看不懂。拼接柜板、门板,都有标写木板次序的符号。从一到十,不是汉字,更不是阿拉伯数字,有点像又不是罗马数字。我好奇地问木匠师傅:“你老人家标咯顺序,吗跟画桃符样?看不懂呃。”师傅很神秘地说:“鬼崽子,咯是鲁班师傅传下来的,乱讲得罪祖师爷,会肚子痛。”没有问个明白。下次木匠来屋场,我又问来问去,师傅仍是无可奉告。
农家屋檐搭屋角,家什容易混杂。毕竟也是财产,又要互相借用,标记归属,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终归能避免无谓的纠纷。
家里打水桶、脚盆、饭兜,新做了桌椅板凳,新买了棕皮、粽叶斗笠或是纸伞,趁着还未油桐油,在显眼处用墨笔写上“某某记”字样。一个屋场多为同姓,姓氏便省去,某某即为户主的大名。桐油干了,字迹稍稍模糊,归属却一清二楚。有了桐油的保护,日深年久,“某某记”依然是“某某记”。箩筐、筛子、簸箕、撮箕之类的篾货,不需油桐油,直接用墨汁或油漆标写。挑错水桶、箩筐,拿错斗笠、撮箕,背错锄头、耙头,依着“某某记”,便可物归原主。
那时,洋铁皮桶子时髦又贵重,样式都差不多,最易混杂不清,更需作标记。墨笔字管不了多久,便用红洋漆标写。白铁皮上的红字太打眼,一般写在桶底的外侧。同款的混在一起,倒转桶子查看“某某记”,分清归属谁家。记得我住校上高中,买了个新铁桶,父亲沿袭乡下的习惯,也用红漆在桶底号上了我的大名。后来发现,同学们的铁桶也都如此。
那时乡下办红白喜事,都需借用左右邻舍的桌椅板凳、碗筷炊具。瓷碗大同小异,借来的碗,不易分辨为谁家的。因归属印记的需要,乡下瓷匠便极少修补瓷器,大都为瓷碗錾字和整修陶器。进得屋场,瓷匠放下工具挑子,高声招揽生意:“錾碗整缸瓮哦!錾碗整缸瓮哦!”女顾主搬出新买的大碗小碗,一番讨价还价后,师傅系上围裙坐上凳子,拿出各色金刚钻和钉锤,排场开工。
叮当叮当,金刚钻尖破蚀碗底的瓷面,留下如秤星一样的麻点,连缀成“某某记”字样。錾字是个细致活,耗神费心,稍不留神,便会凿裂甚至打碎瓷碗。师傅做事时,忌讳有人吵闹,偏偏我们小孩子叽叽喳喳。师傅推低老花镜,和颜悦色劝说:“你咯些鬼崽子,去开边点子啰,耳朵都嘈聋哒!”
遇上笔画多的字,师傅都用乡下习惯的自行简化字,减省不少工时。我仗着自己读了几册书,对师傅提意见:“师傅,冇得咯个字吧,我吗不认得?”师傅若无其事说:“小徕几呃,咯是简化字嘞。”我教育起师傅:“语文老师讲,乱写简化字,作文要扣分。”师傅笑笑说:“我只读咯多书,你听你语文老师的冇错。”邻舍办喜事,有时帮着清理借来的碗,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简化字,心里并不纠结,觉得有字总比无字好。后来住校读书吃统餐,每人一个铝饭钵,边口錾上学号,当作“某某记”。端钵子吃饭,有时记起錾碗的师傅,觉得钵子也亲切了。
各家鸡鸭,清早出埘就成群结队,去町里山里觅食,晚上,凭着天生的悟性,归埘进宿。常有呆萌的小鸡,跟错队伍,进了别家鸡埘。女主人清点,发觉数量不对,也不着急,习惯去问邻舍主人:“我屋那只雷头鸡仔冇进宿,看在你屋鸡埘冇?”邻舍打开鸡埘盖板,就着煤油灯火,果然发现那只鸡混在里面。原来,刚孵出不久的小鸡,身上无法印字,各家用红蓝黑墨水,在绒毛上染一小块“号记”。同批出壳的多,红黑蓝三色区分不了,女人们默契,以同色墨水,东家号鸡头,西家号鸡尾,你家号鸡脖,我家号鸡翅。“号记”无字,实则也是“某某记”,小鸡进错埘门,便可轻易找回来。
有一种印象最深的标记工具,叫做石灰印。四角形木箱,不足一尺见方,底板有镂空图案,带活页锁扣的面板上钉有木抓手。石灰印不印证归属,而用作防盗。队上尚未完全晒干的稻谷,下午收拢成小山似的谷堆。收工之前,父亲提着装满石灰的大印,围着谷堆低坡,盖上十来个印记后,锁回仓库。担心晚上落雨,轻轻盖上稻草,印迹仍旧完整。石灰印如图章般清晰,威严地标示:集体财产,封印勿动!清早,若发现石灰印迹毁坏,无疑有窃贼偷谷,抑或有守谷者监守自盗之嫌。
队里稻谷入仓,落锁之前,也会戳上几个石灰印。父亲执掌石灰印十余年,晒谷坪清泰平安,粮仓却失盗过一次。窃贼扭毁两把大锁,依石灰印损毁程度,估计偷走一担谷。父亲作为队上的保管员,掌管其中一把钥匙,心里又焦急又愧疚,唯恐社员猜疑自己。公社公安特派员来过,发现沿铁路一路撒落谷粒,研判是外贼所为,父亲心里才释然。
“某某记”记录乡民智慧和乡风秩序,现在想来,不仅仅是有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