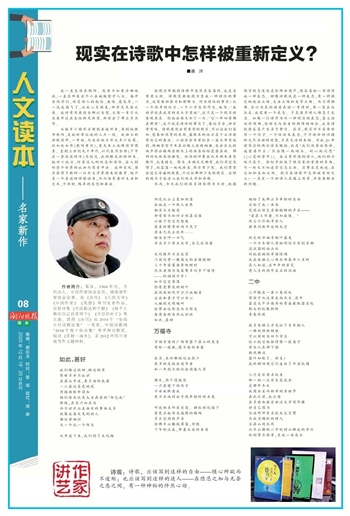■聂 沛
我一直生活在衡阳,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一直在祁东这个小县城做留守人士。高中老同学们、同是诗人的起伦、鹿鸣、聂茂等,一一远走高飞了,让我心生艳羡,却并无失落之感。我时常用康德来聊以自慰:大哲一辈子从未离开过出生地柯尼斯堡,却写出了那么多杰作。
从故乡小镇风石堰到县城祁东,再到地级市衡阳,是我时常往返的三点一线。我独立的诗歌写作,一开始,与这些地方并无多少瓜葛,比如处女作《歌唱黄河》,毫无本土地缘诗学因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代表作长诗《下午是一条远逝的河》为标志,我的眼光折转回来,把对小地方、对身边人的叹息和爱怜,溶入到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与思索中去。这种变化,居然获得了衡阳一位非文学界朋友的激赏,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诗歌读者,然而保有着对生活和艺术,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把现实照搬到诗歌中显然是容易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诗歌需要把现实变成一种诗性的事实,这需要洞察力和理解力。何为诗性的事实?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小学生写作文,他写:“我的学校在我家的东头半里地”,这只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但他后面又加了一句:“它一年四季都在那里”,这个就是诗性的事实了,看似多余,却非常有味。诗歌要写出有意思的现实,可以让我们感知、想象和思考的东西,最根本的地方在于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小说家余华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两辆重型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发出巨大的响声将公路两旁树木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那种对死麻雀的描写,给你的印象会比车祸本身更强烈,也更持久。因为,车祸天天都有,我们司空见惯了,而震落一地死麻雀,则非常少见。我们常常会遗忘普遍的现象,只记住那种少见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才能进入我们的文学和诗歌。
然而,今天我们的很多诗写得并不好,把握现实的态度还是依样画葫芦,很容易把一首诗写成一种表态。好像诗歌就是一种表态,有一种固定的政治立场、生活立场和美学立场。而习惯懒惰、自以为是的读者在读一首诗时,第一需求往往是:我需要一个表态。于是很多诗人都急于表态。如果一行诗作为对一种现实的表态,意义指向很明确,恰好又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这类诗就很容易产生名言警句。其实,现实并不需要你用一个句子、一个结论来表态,千万琐碎的问题和无尽浮动的遐想,才是生活的本相。用我20年前写过的两句诗来概括,就是“我们徒劳地坚持,遥望着什么∕然后像一块峭石,耐心地沉思”(《心灵的劳作》)。真正有价值的诗人,他们的兴味只在于:你似乎抓住了现实某些重要的东西,可一时又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实事求是地说: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现实在诗歌中怎样被重新定义?一直是一个好诗人在路上思考、并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