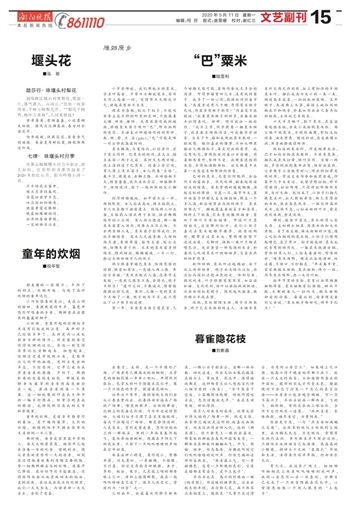出巷子,左转,是一个半圆形广场。广场旁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淡紫色的梧桐花像一串串小喇叭,开得热烈张狂,巴掌大的叶子隐藏在花丛中,像一只只绿色的手掌,提溜着花喇叭。
往年这个季节,每到傍晚大妈们会从小巷鱼贯而出,托着移动音箱来广场跳广场舞,嘹亮的歌声,欢快的舞姿,比树上的花朵还热闹。可今年受疫情影响,大妈们似乎习惯了在家里搞锻炼,每次下班路过广场时,都是静悄悄的。人走雀来,有时走着走着,忽然惊起地上的一群麻雀,噗的一声麻雀轰然起飞,集体奔向梧桐树,隐藏在夕阳之下的花丛里,只留下一片叽叽喳喳的声响在空中回荡。
麻雀这种小精灵,身形瘦小,骨骼单薄,羽毛蓬松,一身赭褐,不抢眼、不讨喜。但它生存能力却极强,虫子、草籽、稻谷、果子,凡是能上嘴的都要啄上几口,再加上抱团群聚,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很多人厌恶它,曾被列为“四害”之一。
儿时放牛,我最喜欢用弹弓射麻雀,一颗小石子射出去,雀群一哄而散、四处逃逸,然后又仙女散花般落在枝头上、草地里、花丛中,落得遍地都是。这种场景总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麻雀》,“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真是生动有趣,好玩得很。
很多人对麻雀的感情,就像大家对待大妈的广场舞一样,既爱又恨。画家徐悲鸿就是这样的,他喜欢画麻雀,而且还画得出神入化,他的《柳雀图》,你只要见上一眼就会喜欢。那柔软的柳枝在春风中摇曳发芽,一群麻雀在柳枝间翩翩而飞,平飞、侧翻、俯冲,形态各异,仿佛能听到它们叽叽喳喳的欢叫声。但徐悲鸿却这样形容麻雀,“麻雀最土气,它一身赭褐色,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它连走路都没有姿态,是个土包子”。
齐白石也是。高兴的时候画一幅《稻雀图》,用温暖的赭黄色,渲染出秋天的丰饶,再勾勒几笔,画只麻雀立在稻茎上,题款是“凡事只求过得去,丹青何必苦言工”。如果喝上几口酒,他高兴得干脆连稻草都不画了,就画一只大大的麻雀,头和翅膀用喜庆的中国红,腹部的羽毛才用青灰色,题款绝对不会忘了抒发一下自己的豪言壮语——汝身虽小能分鸡食鹤粮。可一旦不高兴了,齐白石就画一群麻雀,飞的飞、栖的栖,有的还在地上啄谷粒,当然不忘对麻雀一通骂:“麻麻雀雀,东啄西剥,粮尽仓空,汝曹何著。”
陈胜更可恶,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让麻雀的地位立刻低到尘埃里,成为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代名词。幸亏麻雀并不理会这些,只顾快乐地转动自己乌溜溜、亮晶晶的小眼睛,精神头十足地“集团式”作战和生活,活得虽然简单卑微,但却快乐无比。
有几次,我站在广场上,细细倾听梧桐花上麻雀叽叽喳喳的欢叫声,我的心会忽然沁出一丝喜悦,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只麻雀隐藏在花丛中,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别人眼里的“土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