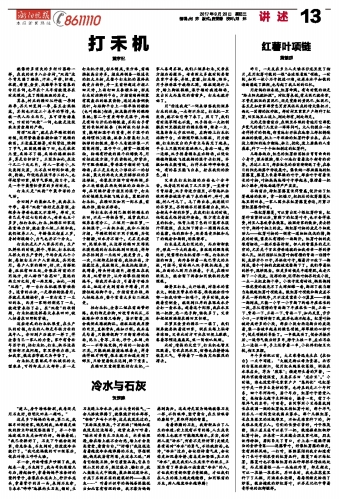就像许多消失的乡村旧器物一样,在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双抢”这个曾充满了酷热、汗水、辛劳、忙碌、收获、希望、金黄、浅绿等丰富意象的专用名词,也早在十几年前就遗弃在时光深处,成了陈迹斑斑的历史。
算来,村庄的稻田从种植一季到两季,再又回复到一季,甚至全然抛荒,其间也不过三十来年的事情,也就一代人而立而已,真可谓沧海桑田。旧时的“双抢”一词,也就是这段农业黄金期的产物。
所谓“双抢”,就是在早稻收割的时候,还得紧接着备耕和插下晚稻的秧苗。正逢盛夏酷暑,时间紧迫,耽搁了节气,纵然晚稻插下田,也是秋收无望,或结不了穗,或结的穗短秕谷多,算是白忙活了。正因为如此,在这十几二十天之内,村人一家老小,从天亮到天黑,无不在田野间忙碌,抢收,抢插。即便远在城市务工的人,也得赶紧回家,跟节气赛跑,抢日子。这是一年中最繁忙劳累的乡村时光。
打禾又是“双抢”中最辛苦的力气活。
分田到户的最初几年,我尚在上中学。每年“双抢”恰好是在暑假,全程参与劳动也就义不容辞。那时,父亲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母亲也五十多岁,抬打禾机、打禾、挑稻谷回家这类重体力活,就全靠二姐、三姐和我。我们姐弟三人,年龄依次相差三岁,身材都较矮小,力气也并不十分大。
打禾机是几户人家共用的。生产队解体的时候,耕牛、犁耙、打禾机这几样大的生产资料,平均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由五六户人家构成,共同使用。每户人家的稻田,好、次、劣搭配着,往往有四五处,分散在村前的不同地方,村人称作“杂花田”,最远的两丘田之间,有一两里路。如此,一到“双抢”,那一台打禾机就很紧缺抢手。通常的办法,一是排班轮流着用;再就是见缝插针,当一家打完了一丘田的禾,而另一家刚好割完了一丘,就赶紧来抬了去。在“双抢”的收割期,打禾机就这样每天来来回回,被人抬着在田野间穿梭。
这些老式的打禾机很重,在生产队的时候,打禾的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分田到户后就不一样了,得全靠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家中有青壮年男子的,抬打禾机、打禾、挑谷这类重活都不成问题。家里劳动力弱,比如我家,做这些事就尤为辛苦了。
打禾机是装配式半机械化的大型农具,可拆卸成三大部件:其一是打禾机方桶,杉木制成,长方体,前端挡板高出许多。桶底两侧各一根通长的粗大木枋,是整个打禾机的最终承载受力构件,并一直前伸超过方桶三四尺许,上面钉四五条横木枋,形成打禾时站脚的平台。方桶前端两侧装有圆盘状的漆黑齿轮,通过扁条钢铁连杆,与站脚平台上一根单独的横枋(也叫踩板)相连,组成能升降的踩踏系统;第二个重要部件是滚子,两端是有均匀开孔的铸铁盘,其间由手臂宽的长枞树板条(枞树板比杉木板重,能增加滚子的重量,利于滚子的旋转惯性)连接,板条上密集钉上尖拱形的粗铁丝,整个儿看就活像一只圆筒刺猬。滚子中心,横贯一根圆钢轴,轴端有拧旋的漏斗状铸铁耳,用时抬放进方桶,卡在齿轮处,拧紧后,即可驱动踩板,带动滚子顺时针飞速转动;其三是五块大小形状不一的杉木板,最大的两块大致呈梯形状的多边形板,安装在方桶中前部两侧,其余三块镶嵌在两块侧板的后面和上部,共同维护着方桶里的滚子,打禾的时候避免谷粒飞溅出来。装配好的打禾机,在稻田里如同一间木屋,前拖后推,能让其移动。
将打禾机弄到已经割倒稻禾的水田,不是一件轻易事。通常我们三姐弟各有分工,三姐用一担谷箩,一头挑滚子,一头挑木板,我和二姐抬方桶。早稻收割时不同于晚稻,为便于翻耕,田水并不溜干。尤其是水浸田,泥深水深,从这样的稻田里将泥水浸泡透的打禾机拖到田埂边,拆卸后再抬到另一丘远田,就更费力。每一次,二姐都是抬前面,我抬后面。方桶覆过来,底板朝天,她先托起桶后,我蹲着,将头伸进桶内,桶壁压在我两肩,双臂伸开,从外面攀住桶侧的拖耳。待我用尽全力,弓着身子略为站立,她这才走到前面半蹲着,用肩膀抬起站脚平台。方桶前重后轻,两人抬起来后,整个重量大多由二姐承受。
抬打禾机,全靠二姐在前面带好路。我们都是赤脚,田埂弯曲而仄,石板路和砂石路又咯脚,若不留意,还会栽倒或踢破脚趾。桶板压进我肩膀的肉里,直抵骨头,痛如刀割。我头总是勾着,只能俯视脚下不断前移的地面,泥土、青草、石块、砂子、水圳、沟坎……不停地变换,外面的一切全然不见,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走,浑身痛得龇牙咧嘴,根本就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只盼望着快点达到,释下重负。
在稻田里重新装配好打禾机,一家人各司其职。我们三姐弟打禾,父亲在方桶后面撮谷。母亲则大多数时间要留在家中弄茶、弄饭、煮潲、扫禾场、晒谷。用手推动滚子旋转几圈,踩板随连杆上升,踏上脚板猛踩,滚子顿时疾速转动,发出巨大而急促的嗡嗡声。打禾也就开始了。
用“你追我赶”一词来形容我们姐弟打禾的状态,一点都不为过。打禾机一旦发动,就不让它停下来了。烈日下,我们有时连草帽也不戴,双手掐住一大把割躺在田里摆放好的稻禾根部,俯身一立,便急匆匆大步往回赶,左脚踏上打禾机站脚平台,右脚随即踩上踩板,用力蹬踩,打禾机发出的声音立马高亢了起来。平台上只能同时容纳两人,各站一端。脚一边踩,双手掐着稻禾左右转动,以便让稻穗都能被飞速旋转的滚子击打到。谷粒如雨点般喷溅,打得木板哔哔啪啪直响,有的甚至能飞出来,射在我们的脸色,痛!
父亲在打禾机桶的后面也十分辛苦。他身边同时放了几只谷箩,一直俯首弓背站着,双手伸进方桶里,不停地扒拉梳理那些被滚子旋下来的稻秆、碎叶、稻穗,村人叫毛丫。毛丫捧出来,放进较旧的谷箩里。再将稻谷用撮箕撮出来,倒入全新或半新的谷箩。在我们打禾的时候,他便总是保持这种姿态,很少有立身挺直的机会。他背上退了色的旧蓝布衣服汗得透湿,在太阳下烤出一圈圈西瓜纹的盐霜。他的脸和手,还要忍受谷粒和毛丫的溅射和撕割,划痕密布。
打禾总是先打近处的,而后渐渐散开,形成一个大的扇面。当往返的距离较远时,便需将打禾机前移一程。打禾机方桶的四角,向外各伸着一块巴掌大的木板,叫桶耳,前面两人双手提托起来,前拖,后面的人则用力推着。于是,在稻田软泥上,就会留下两条如同铁轨的光滑深痕。
酷暑里打禾,大汗淋漓,对茶水的需求大。铜壶里带来的凉茶,很快就会你咕嘟一杯我咕嘟一杯喝干。许多时候,我会提着空铜壶,就近到江岸的泉眼或水井去打一壶水来。趁着这个间隙,我在水里洗一把脸,泡一泡手脚,畅快多了。父亲和姐姐则继续在稻田里忙碌。
谷箩里金黄的稻谷一一满了,我们姐弟就要挑着送回家,倒在禾场上供母亲晾晒。父亲此时方可坐在田埂上歇歇,卷着草帽边扇扇风,吸一筒喇叭纸烟。
此时,晴热的天空下,打禾机也暂且沉默着。它伏在泥水里,仿佛也在静静地恢复元气,等待着下一轮高亢而激烈的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