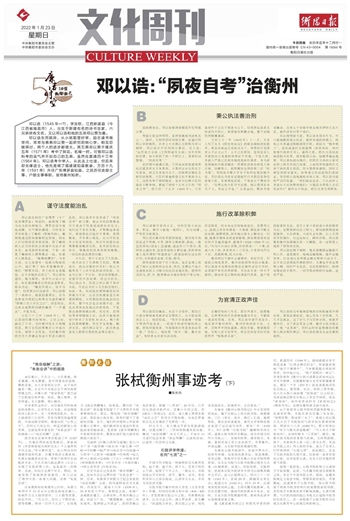■张长元
“南岳唱酬”之游:
“朱张会讲”中的插曲
南岳衡山,五岳之一,山峦重叠,流水潺潺,风光旖旎,是中国著名的道教、佛教圣地,文人学者向往之所。由于南宋偏居一隅,五岳中只有南岳位于南宋政府管辖之内,其衡山的“国家祭祀”更凸显了它的地位和声望。因此,僧人络绎,参学传道;文人接踵,观山题诗。
有学者作过统计,在历朝历代吟咏南岳的诗歌中,以宋代文人为最。在这绵延的诗人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非一人独游而三人结伴,非走马观花而遍观景致,兴高而联句唱和,寓意而托“心性之学”,历时七天而忘归,相互切磋而心有灵犀。这就是南宋著名的“朱张会讲”中的插曲——“南岳唱酬”之游。
故事发生在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 。朱熹在两次面见张栻后,深感南轩(学者称张栻为南轩先生)个人境界和学问之高,“非吾辈所及”,决心拜访当时湖湘学派的代表、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带弟子林用中长途跋涉月余,于九月初八抵达潭州(长沙),实现了朱张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交流,时间长达两个半月。期间,朱熹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双方讨论了理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史称“朱张会讲”。
在朱熹即将结束潭州之行时,朱熹与林用中于11月6日启程往游南岳衡山,张栻作为主人陪同前往。三人踏雪赏景、辩论学问,“凡七日,经行上下数百里。冒雪唱酬,得诗一百四十九首”,后结集为《南岳唱酬集》。如果说,潭州的“朱张会讲”给岳麓书院留下了可贵的学术探索精神的话,那么,期间的“南岳唱酬”之游,则在高山流水间,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诗篇。至今,他们吟诗唱和之声还留在衡山云雾中,他们跋涉的足迹还印影在旅游者的脑海里。笔者按《南岳唱酬集》中张栻写的原序,整理出他们登山游历的路线大致如下:
马迹桥(今衡山西部马迹镇)登山→方广寺→莲华峰→高台寺→望石廪→西岭→天柱峰→福严寺→南台寺→马祖庵→大明寺→上封寺→祝融峰→穷林阁→仙人桥→上绝顶→过南岭(下山)→邺侯书堂(林深路绝未果)→行至岳市(今南岳镇)→再至劲节堂(今祝圣寺)。
历史不会忘记朱张的“南岳唱酬”之游,犹如不会忘记潭州的“朱张会讲”一样。后来,朱熹弟子钟震为了纪念朱张的“南岳唱酬”之游,将马迹桥命名为朱张桥,沿用至今。嘉靖十八年(1539年),33岁的进士尹台,奉朝廷之命,来湖广各地册封藩王。公事完毕,作南岳衡山之游,夜宿方广寺,“慨想晦庵、南轩二先生高风,低徊留之不欲去”,即捐资衡山知县章宣,修建“二贤祠”。20年后,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尹台,受衡山乡民之托,作《南岳二贤祠记》。此后,高人雅士赞颂朱张“南岳之会”的诗文不绝如缕,为南岳厚重的历史文化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时至今日,有人建议开辟朱张旅游线路,在莲花峰下、二贤祠旁修建朱张诗廊,镌刻“南岳唱酬”诗文于其上,于每年11月进行纪念朱张“南岳唱酬”之游的活动,以延续一代宗师之文脉。
石鼓讲学传道:
名列“七贤”之一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起于唐,盛于宋,续于元,普及于明而止于清,延续了千年之久。一般认为,书院制度由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和学田六大部分组成,以讲学为主业,学田为其经济支撑。
石鼓书院乃衡州的邑人李宽(又名李宽中)所建,时间约在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李宽因爱石鼓山川之胜,寻真观构屋读书,以为习业之所。清人罗庆芗、彭玉麟云:“改道院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及招诸生,弦诵其中,本自宽也。”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亦有同样的说法。建于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绿荫掩映,三江(耒水、蒸水、湘江)汇流,地理形胜。蜀汉丞相诸葛亮、唐代文学家韩昌黎在此留下过足迹与诗作。景祐二年(1035 年),宋仁宗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五顷,遂使石鼓书院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当时四大书院之一。至南宋时期,理学勃兴,朱熹、张栻等高士贤人在此讲学,书香衡州,声誉远播,为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
朱熹在石鼓书院讲学,似成学界共识,但尚有存疑。而张栻执教杏坛,情连理顺,史有记载。张栻早年曾在衡山文定书院拜师研读,而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都以理学为圭臬(比喻准则、法度),同根同源,文脉相亲。张栻来石鼓书院讲学不仅可以阐释其胸中之学识,还可以提携后人。绍兴三十一年春(1161年),张栻29岁,跟随其父来长沙;乾道元年(1165年),时年33岁,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持岳麓书院教事,先后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执教8年有余。此时,正是石鼓书院鼎盛时期,张栻来此讲学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嘉靖衡州府志》和现代学者的研究,乾道四年(1168年),湖南路提举常平使范成象“以图志搜访旧志”,得诸葛武侯祠“废宇于榛莾中”,乃率僚属提点刑狱郑思恭、知州赵公迈,“徙于高明而一新之”,并请张栻作《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并手书砌碑。另据衡阳地方史专家郭建衡考证,建安二十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后人在石鼓山南面建“武侯庙”以志纪念,后该庙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体书写),此碑在衡阳保卫战中流失。
由于张栻对石鼓书院的贡献和影响力,在南宋时期,书院在讲堂后建二先生祠,“祀韩昌黎、张南轩二夫子”。张栻入祀石鼓正式开启了书院祭祀与讲学相互借重的格局。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郡守何珣认为“朱子与敬夫讲道衡湘”“乃入朱子于韩张祠内”,该祠时称为“三贤祠”。继后,随着石鼓书院的的重修与改制,又将周敦颐、黄干、李宽和李士真(后二者为乡贤,有创设书院之功)列入祭祀对象,成为了后来人们所称颂的“石鼓七贤”。滔滔湘江,见证了石鼓书院的几度兴废,但张栻一直享有祭祀之誉,自宋延续至清,足见人们对他的喜爱与崇敬。
值得一提的是,石鼓书院影响力至清初才开始衰微。此前,与岳麓书院成北南犄角之势,齐名于中国书院之列。清初,岳麓书院被定为省会书院,凭借其新的地位,声望鹊起,迅速领先于石鼓书院, 而石鼓书院囿于府级书院身份和行政地理因素的局限,其传统学术教育优势不断被消解;至清代晚期,与石鼓同城的船山书院又以道级书院身份后来居上,进一步削弱了石鼓书院作为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