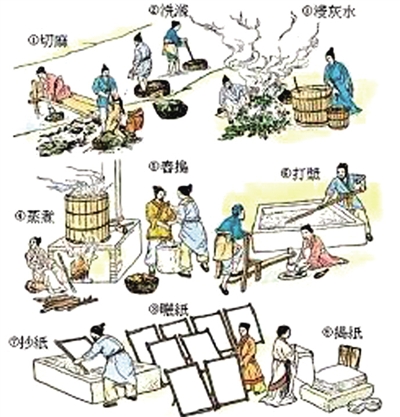1990年,比利时国际纸史学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定:蔡伦是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中国是造纸的发明国。
《耒阳县志》说:“县人蔡伦发明造纸术以来,县内乡民利用造纸技术造纸,历代相传。手工造纸作坊多的10余人,少的2至3人。产品有包皮纸、烧纸、皮纸、湘薄纸、五色纸等土纸。陆运至涟州、郴州、桂阳州、坪石;水运至衡州、湘潭、长沙、汉口。近代的衡阳还是湖南三大造纸中心。”
蔡伦在一千多年前造纸的岁月里,他是如何学会造纸的?他有没有师傅?这个师傅是不是耒阳人,抑或就是他的父母亲?他的舅舅?还是他的邻居?还是他自己发明的?蔡伦之所以能够造出纸来,是否与他在故乡耒阳的生活经历有关?
《湘中记》有一段话这样说:“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萧平汉先生漫步于蔡伦纪念园中,看到了据说是《湘中记》所讲蔡伦造纸留下的石臼,雕刻古朴而显得苍劲,饱经风雪的花岗岩四周斑驳坎坷,伤痕累累,早已看不到当年蔡伦造纸的痕迹了。然而这石臼还在,虽不能考证它的真实性,也不能去否定它的真实性。就是这一个石臼,历经千年也好,还是几百年也成,它代表了耒阳人民对为人类文明作出杰出贡献的家乡先贤的崇敬之情。
衡州酒米闻名朝野
衡阳的名酒——酃醁酒早在西晋建立之前就已产生,三国或许东汉就已闻名中原,或许是船夫们北上随身携带,或许是南下中原人喝了这种美酒后有意带回中原。酃醁酒不仅传入北方,而且由于文人们的有意夸张,演变成了文字。
晋人张载《酃酒赋》有篇最著名的赞颂酃酒的歌赋:“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若乃山中,冬启醇附,秋发长安,春御乐浪,夏设蚁漂,萍布芬香,酷烈播殊,美于圣载信人,神之所悦,未闻珍酒,出于湘东,丕显于皇都,乃潜沦吴邦。”他说,这美酒不论人间王朝的兴废,经历上百代而愈来愈珍美,并明确地指出,这美酒产于湘东郡。
除文人群体,衡阳美酒不断地在政界中传播,成为了人人欲得而不可得的佳酿美酒。有人将这酒给曹氏家族带去,最终进入了王宫,呈现在曹氏小皇帝御膳桌旁。然而,曹氏集团好景不长,司马氏夺取了政权。好酒贪杯的司马氏早已品尝到了美酒,立即被它的浓郁淳厚的香甜所征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后来,这酒成为司马氏家族的日常饮料。
太康元年(281年)司马氏平吴,趾高气扬的司马炎以皇帝的身份带上作为俘虏的孙皓,“临轩大会,引皓升殿,群臣咸称万岁。丁卯,荐酃醁酒于太庙”(《晋书》卷三)。他下令由地方官每年都要向中央王朝进贡,要在太庙祭祖时用。其后,酃醁酒成为司马氏家祭太庙的专用酒。东晋咸安元年(371年),晋简文帝登上帝位之时,也荐酃醁酒于太庙。
南朝以后,“醽醁”称之为“酃酒”,以用酃湖水酿酒得名。酃湖在今市东郊。《北堂书钞》卷一四八“湘东酃水”条引《吴录》说:“湘东酃县有酃水,以水为酒。”左思《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酃醁”。唐李善注引《湘州记》云“湘州临蒸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明冯化时的《酒史》卷上载晋张载《酃酒赋》,标题下注文:“衡阳东有酃湖,酿酒甚美,所谓酃酒。”“酃酒”产于衡阳湘江东岸酃湖一带,以优质糯米取酃湖之水酿造而成,色泽金黄,浓郁香甜,独具风格。历史称“醽醁酒”,后世称之“酃酒”。
“醽醁酒”的出名,由于有与众不同的衡州大米。从魏文帝曹丕的“长沙有好米,十里飘香”,到“味重新城,香逾涝水”的衡阳米,是这里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衡阳与长沙一样,也是一个出产好米的地方。“魏文帝与朝臣书曰。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时此。新成粳稻邪。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艺文类聚》卷八五)长沙好米固然指长沙,但同时也应泛指湖南一带。衡阳也有好米。南朝梁庾肩吾的《又谢湘东王赉米启曰》说,湘东王的米“味重新城,香逾涝水。连舟入浦。似彦伯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窃以农夫力耕。时逢俭岁。疏贱时泽。必取丰年。椓斛泻珠。嘉闻陶量。翻庭委玉。欣见马圖。”(《艺文类聚》卷八五)。
“新城”是三国魏黄初元年设置的郡名,辖境在今湖北房县、保康一带,那里产的米味道特好,是一种品牌;涝水在今陕西户县,那里产的谷子很香,也是一种品牌。所以,庾肩吾用这两种名牌产品来形容湘东王送的米。湘东王的封地就是衡阳,地方所纳租税一般都是粮食,也就成为湘东王的俸禄,所赠送的米通过运河运入京师。如此,这米先沿湘江由南北去,再东上长江,直达南京,可以说湘东王所赠送之米正是衡阳生产的。
衡阳米数量较多,零陵有米外调,桂阳也是盛产大米的地方,因而粮食十分丰富。“桂阳行贤书赞曰。成丁。郴人。能达鸟鸣。为郡主簿。与众人俱坐。闻雀鸣而笑曰。东市辇粟车覆。雀相呼往食之。众人遣视。信然。”(《艺文类聚》卷八五)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说明当时这里市场繁荣,粮食买卖正常。
魏晋南北朝,境内使用占城稻、红米冬黏等水稻良种。南朝刘宋时期,南方开始种植双季稻。双季稻种植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最早的了。宋元嘉十六年(439年),耒阳已试行连作与间作稻。盛弘之《荆州记》载: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游百里水稻重种,农民在早稻成熟前,利用旱土育秧,待早稻收割后再插晚稻,甚至有一年三熟的。
南朝的种种乱象致使经济衰退
魏晋南北朝的农业生产状况并不理想,相较于两汉时期是历史的倒退,其一是两晋以后大多实行分封制,土地国有的占有形式及分封制的推行,劳动者失去生产积极性;其二是战争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劳动力的减少是造成这一时期生产倒退的根本原因。
西晋灭亡时,司马氏子孙就分封在零陵,成为一个食邑地主。“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菸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宋书》卷三)整个郡郡民都成为司马氏一家的私人佃户。
南朝的衡阳境内先后封过王侯、郡公与县公。刘宋封刘彧为湘东王,食邑二千户。齐封萧子建、萧宝晊为湘东王。梁封萧绎,陈封陈叔平、徐度为湘东郡公。刘义季为衡阳王,食邑五千户。齐封萧钧,后则萧子峻为衡阳王;梁封萧畅、萧元简;陈有衡阳王陈伯信、陈昌;梁有永阳嗣王(祁阳曾属永阳郡),衡阳嗣王,桂阳嗣王……县有县公,如临蒸县县公、桂阳县公、桂阳县侯、祁阳县子,祁阳县侯等等。
陈朝侯瑱封湘东郡公,食邑四千户。后来“改封零陵郡公,食邑七千户”(《陈书》卷九)。南朝零陵七县才三千多户,衡阳才五千多户,差不多就是衡阳加零陵两个郡的人口。那么,两郡人口都成了他食邑的佃户。
还有一种土地占有情况是由政府赐予宗教土地。这些赐户庄田与前面的封户性质相似,是一种将国家土地的租税分给寺庙的方法。不同的是,这是赐而不是封。封必须是因功、劳、勤、勋,或是皇帝的亲属,而当时的寺庙衡岳观什么也不是,所以只能赐了。赐户与封邑性质相同,他们只有收取租税的权利,而没有治理民众的权力。
从史料分析,南朝的衡阳田地基本上是国家土地。分封、采邑的食封贵族以宗族形式占有。这种土地占有形式,加上宗族式的统治,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发挥不了的。由于这样,粗放农业在当时的江南衡阳地区是主要形式,生产力不高,产量有限。后来,由于战乱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南朝社会生产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东晋时“湘州刺史……郡十,县六十二,户四万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南朝的刘宋时“长沙……领县七,户五千六百八十四,口四万六千二百十三。”“吴昌侯相,后衡阳内史……领县七,户五千七百四十六,口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一。”桂阳“领县六,户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万二千一百九二。”“零陵内史……领县七,户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八。”“营阳太守,江左分零陵立。领县四,户一千六百人八,口二万九百二十七。”
上述人口统计都是《宋书》卷三七所说衡阳地区的人口,不论长沙、衡阳、零陵、桂阳之间的离合分化如何,其总体人口都是很少的。如最后一条资料,营阳四县,每县人口平均才5000多人,桂阳六县,人口平均还不到3700人。与东汉长沙平均每县81000多人比较,不足其二十分之一。因此,政府有奖励生育政策。南齐明帝五年(498)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南齐书》卷六)。
人口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手更少,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物质财富少,再加土地大部分私有,让魏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倒退时代。
诸多县级政权机构的设置标志着繁荣
自西汉至南朝六百余年,衡阳城区先后设置过酃县、湘东郡、临蒸县、衡阳王国地。从秦汉时的酃县到三国时的临蒸县,成为今天衡阳市的胚胎。
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西汉至隋朝时衡阳地区的县级政权机构有衡阳县(今衡山)、衡山、酃县、临蒸、耒阳、永昌、祁阳、重安、新宁、新平、承阳、新城等县名。而耒阳则时属桂阳,时属衡阳,祁东因属祁阳县,则归零陵管辖,衡山、南岳与衡东旧属衡山,分合离散,千百年来一直变幻不定。但不论这些变化如何,从这些县治遗址来看,它们都坐落于河水之畔,甚至位于二水或三、四水的交汇处,这是古代社会城市设立的基本特点。
地理交通的便利是古代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衡阳作为湘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与最大的城市,陆路水路四通八达,古往今来,衡阳既是政治重镇,也是军事重地。两汉时期衡阳经济发展迅速;三国之后,衡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就是县级政权机构的大量设置与县级城治的普遍建立。
吴太平二年设立的县城——衡阳县。这个衡阳就是今衡山县,县治在大源渡。与今常宁市所在地设立的新宁与新平同年建立,是吴政权加强对衡阳地区控制的反映。在市区湘江东岸,则有西汉时期的酃县县治遗址。沿蒸水向西北而去,则进入今衡阳县,这里曾有过西汉时期的承阳县县治。沿蒸水主流北向,经台源、渣江折而向西,则到达洪罗庙、金兰寺。这个金兰寺,在西汉时曾是承阳县的县治所在地。
从衡阳入耒水,南下郴州,则有泉溪、新市、耒阳等,新市曾为南朝陈时的新城县县治,耒阳曾是三国时蜀国庞统曾经任过县令的地方。从衡阳沿湘江西行,就到达今常宁市境。这里有三国时曾经建立过的新平县治。县治在今柏坊镇内的双白村,位于湘江南岸的湘水拐弯处。这里三面环湘水,只有南向开阔,是个用天然屏障来进行自我保护的城镇。
再往西,就到达今祁东县,这里也有一座古县城祁阳县城,位于今祁东的金兰桥。《水经注》记载:“余溪水过县南,入于湘”。余溪水在哪里?“余溪水即今祁东的白河。民国时期李馥《祁阳县志·山水志》引李建勋《祁阳故城考》具体指出祁阳古城在今祁东县的金兰桥。沿湘江继续西行至今祁阳县城,则有祁水注入湘江。溯祁水约行100里,则到达砖塘,这里是永昌县县治。位于今祁东的砖塘,紧傍祁水。永昌县也是三国时设置的。
上述县治有相当数量是在吴太平二年前后匆匆建立的。从目前衡阳地区各县的城池建筑情况来看,县治城楼或城堡,考古发掘有常宁市城治遗址。祁东金兰桥常登第的故县祁阳县衙,三国东吴孙皓元兴元年至天纪四年(264—280年)期间,祁阳县城设在这里,金兰桥作为一个老县城,一直到隋王朝都是祁阳县城所在地,唐武德年间迁至今祁阳。另一座古县城——永昌县城也在祁东境内。
从这一时期出现的县名来看,祁东的永昌,意为永远昌盛,新城、新平、新宁之“新”,意味着刚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宁”是安宁、宁静,不再出现反叛事件;“新平”是刚刚平定、消灭及镇压了一次反叛;“重安”是重新安定;“常宁”是永远宁静与长久平和。从这些命名的字来看,一批新的县级政权正在建立,这表明统治阶级的力量加强了,他们对衡阳境内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报记者胡建军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经贸史述》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