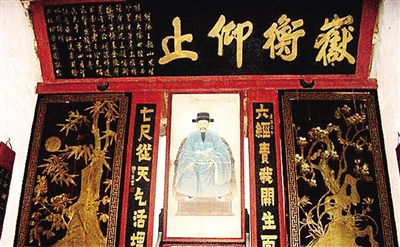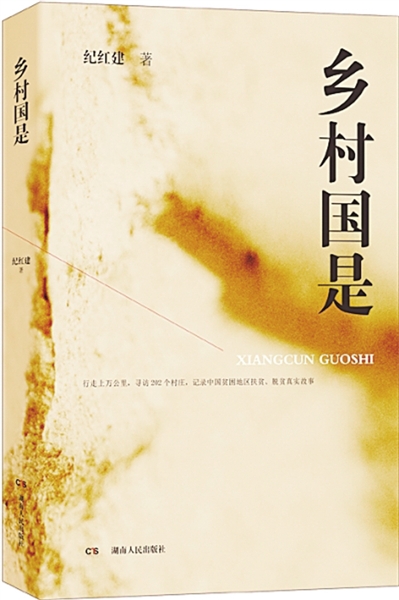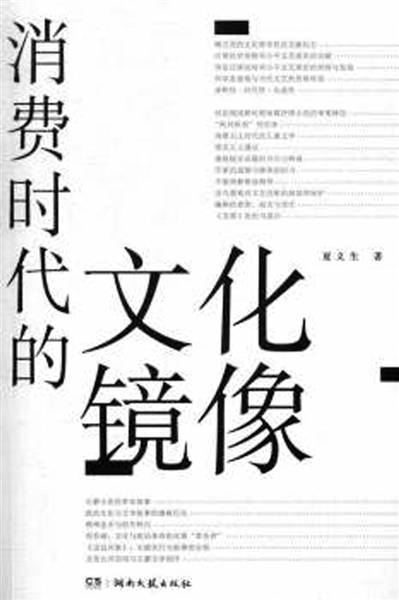夏义生:重振文艺湘军雄风
■林乐伦
林乐伦:夏书记,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雁鸣故里》一书目前已编辑完毕,今天这篇采访稿是付印前的最后一篇稿子。去年4月份,您应邀写的《潭水千载思悠悠》,是一篇很有诗意且考据严谨的文章,是散文也是论文,不知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夏义生: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大家知道,我主要写一些理论文章,平时很少写散文。去年应您之约就家乡记忆写一篇文章,我开始想写常宁一中旁边的培元塔。这座古塔在我心目中的印象非常高大,感觉它就是常宁历史文化的象征。但后来在写作过程之中,感到积累还不够。我是从常宁一中考入湖南师大的,岳麓书院就在湖南师大旁边,就自然而然联想到了岳麓书院,我们常宁人王祚隆做过岳麓书院的山长。
林乐伦:您的文章中,重点写到了王祚隆这个人,也写到了王船山、余西崖等历史文化名人,您认为常宁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是哪几位?
夏义生:常宁历史上文化名人很多,但王祚隆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才华横溢,年轻时,诗名广播湖湘大地,而且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公认,袁廓宇推举他做岳麓书院山长。他在岳麓书院山长这个位置上长达七年,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文化主张,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王祚隆品德高洁,不逐时流,是士子的典范。
林乐伦:在文中您也谈到了王船山避居常宁的故事,今年是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您能用简短的文字概括您心目中的王船山吗?
夏义生:王船山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使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得到凤凰涅槃式的新生,他是近现代湖湘文化的开拓者。
林乐伦: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我们市委市政府要举办一系列活动,您对这系列活动有什么好的希望与建议?
夏义生:市委市政府对船山学的高度重视与推动,令我感佩。因为在衡阳这块土地上,我们把船山先生这面文化的旗帜高高举起,把船山学的精髓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对衡阳的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衡阳引以为骄傲的,有一座名山,这就是南岳;但是衡阳还有另外一座高峰值得我们骄傲,那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王船山。
纪念船山先生,首先要挖掘、研究和弘扬船山精神,以滋养我们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建设,实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伟大使命;其次要从物质空间重塑船山精神的载体,强化对船山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加大船山文化园的建设力度,通过这种物质空间的建设,为后人更好地认识、了解船山先生提供条件。
林乐伦:您曾在南华大学当老师,后来到省文联当领导,这种角色的转变,您认为有哪些变化与不同?
夏义生:我的青年时期,是在衡阳医学院和南华大学度过的。高校是文化氛围很浓的地方,接触的都是大学里面的老师和青年学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常常跟衡阳医学院的学生一起谈论诗歌,讨论文学。跟老师们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医学方面的常识,特别是中医学的一些理论知识,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充满了哲理,蕴含着对人的整体性认识。中医研究注重宏观,重视整体;西医研究注重微观,重视个体;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我的思维方式影响较大;只有多角度、多维度才能把事物认识清楚,这是在衡阳医学院、南华大学得到的重要收获。
我后来调到省文联,这实际上是实现了我的夙愿。在省文联我参与了《理论与创作》的编辑工作,今年又和同事们一起将原来的《创作与评论》更名为《文艺论坛》,将《新故事》更名为《湘江文艺》。能够主编一本理论与批评刊物和一本创作刊物,这是我的荣幸。我也因为编辑文艺刊物和负责文艺工作,非常高兴接触到了全国文学艺术界一批领军人物,能够跟他们学习就是对我的一个巨大提升。从事文艺工作,更加接近我心中的理想。
林乐伦:能谈谈您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的,还记得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吗?
夏义生:具体是哪一年发表习作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参加工作不久,在衡阳医学院的校报上发表了诗歌和杂文。我读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诗歌,尤其是新诗。在大一、大二时,当我们接触到《诗刊》《星星》上面一些青年诗人写的朦胧诗,那真是如饥似渴,一篇一篇地抄下来。后来我参加了湖南师大朝暾文学社;大学毕业后来到衡阳医学院工作,也经常跟学校文学社的青年学子们在一起写诗谈诗,为文艺爱好者开过诗歌讲座,讲过我心中的诗神徐志摩,也讲过当时很火的汪国真。我还担任文学社的刊物《花药春溪》的指导老师。第一篇理论文章是《试论我国新时期短篇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于1986年。
林乐伦:读大学时,你最喜欢的是哪几个诗人?
夏义生:我最喜欢的诗人有顾城、北岛、舒婷、欧阳江河、杨炼等。那时,我对诗歌理论产生了好奇,一遍又一遍读“三个崛起”(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吉林大学徐敬亚分别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三篇诗歌理论文章,为中国朦胧诗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美学诠释与理论支持)。这三篇文章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它吸引我走上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
林乐伦:您是我们衡阳本土走出来的学者型领导,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您是怎么处理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的?
夏义生:文联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很多研究任务需要挤时间来完成。比如开展文艺湘军研究。当时我担任《理论与创作》执行主编,开了“今日湘军”栏目,就是研究推介活跃在文学艺术界的湘军领军人物。为了做好访谈,只好逼着自己利用休息时间去做功课,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我记得第一个访谈的就是我们衡阳老乡唐浩明先生。为了做好他的访谈,我把他的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全部读完。读完之后,还得找相关研究文章读,了解学界对他的看法;还要找唐浩明先生自己的创作谈来读,了解他的创作思考,最后才开始对他进行访谈。后来访谈了彭燕郊先生、音乐家白诚仁先生、谭谈先生、阎真先生、王跃文先生等。从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来讲,对文艺湘军的研究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林乐伦:好像您的博士论文是以王蒙作为研究对象?
夏义生:我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就是王蒙文学创作研究,这是因为做学位论文的需要。我在湖南师大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时,博士论文的选题是王蒙研究。我很喜欢王蒙先生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文革前的小说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革后期有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新时期以后有中篇小说《蝴蝶》和《相见时难》,长篇小说有《活动变人形》,这部长篇小说是他的泣血之作。还有“季节系列”小说,带有自传式意味。我的博士论文《王蒙小说流变与当代政治文化》还未正式出版,原因是自己认为这篇论文写得还不够扎实,还想再改写一遍,这一搁置有八年了。
林乐伦:您曾做过“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专题讲座,能谈谈您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吗?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对文学的影响。
夏义生:对文学的研究大体可以从文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去研究。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外部因素当然就有政治,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又可具体从政治制度、政治人物等来研究。比如,中国当代文学里面有好多作品出版之后又进行改写,大多是因为它与政治环境不相符,它要适应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去改写。如果我们把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环境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就是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在研究王蒙的小说时,我从政治文化这个角度来考察,它是怎样影响了王蒙文学创作的姿态?我研究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从王蒙这个个案开始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
林乐伦:有人说,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它在近现代形成了一个高峰,很难超越,你怎么看?
夏义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看来,某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不一定经济上的高峰期就是文化上的高峰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也经常听到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知道,当国家、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必然激发这个民族的有识之士,比如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这个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未来、前途与命运作出深刻的思考,他们思考的成果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文学高峰、艺术高峰。至于文学艺术的高峰是不是很难超越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同时代的文艺高峰犹如五岳之于中华大地,可以并峙,不一定追求超越。
林乐伦:2014年,您出版评论集《消费时代的文化镜像》得到文学批评界的好评,您能谈谈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家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
夏义生:这本书里面的文章全都是2014年以前写的,出版的初衷,是纪录自己在文学艺术道路上的足迹。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文学艺术才能真正实现从高原迈向高峰。
文学艺术有双重属性。一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二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属性。我们不能做市场经济的奴隶,要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具有双重属性,不能只讲商品属性,不讲它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文学艺术家不能够只盯着市场,只望着消费者对自己作品的购买,还要想到我们的作品给读者(观众)有多少精神上的正能量,能不能够在人类精神空间构建起希望之塔,或者在个体精神困顿的时候,点一盏灯,让它去燃起对自我、对人类的美好期待。文艺作品要能温润心灵,而不仅仅是满足消费的需要,还要引导文学艺术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新时代我们每一个文学艺术家的责任与担当。
林乐伦: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文艺评论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
夏义生:首先是思想上有较高的素养。如果一个评论家,他的思想资源是贫乏的,那么他就无法深入地去理解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就很难洞见文学艺术细微的光亮。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要打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三方面的根基。其次就是在学术上应该有责任担当。做文艺评论是一件清贫而又清苦的工作,要把它当作一份事业去追求,才能守正创新。再次就是在品格上做到真诚。真诚是一个评论家最宝贵的品格。没有真诚的品格,就会人云亦云,就不可避免陷入人情评论、红包评论、表扬式评论的泥淖之中。
林乐伦:您认为当前文艺湘军最值得肯定的和最缺失的是哪一点?
夏义生:从文艺湘军整体来看,我想最值得点赞的就是在思想上敢于发先声、举旗帜,敢于勇立潮头、做时代的弄潮儿。这种精神跟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一致的。文艺湘军目前最缺失的就是原创力不够强。与兄弟省市比,我们的文学艺术在原创力上是有差距的,这不是说某一部作品,而是体现在整体水平上。
林乐伦:今年,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论界好评如潮,把湖南誉为报告文学大省,你是如何看待的?
夏义生: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是我们湖南近年来报告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湖南和全国一样,正在打一场脱贫攻坚战。这场战役将深刻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他把这样一个伟大事件,用自己坚韧的行走和灵动的笔触记录下来。他的这部作品用全景式的方式记录大半个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生动的细节和鲜活的人物,这在报告文学领域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这种写作要求作者付出很多,要去走访一个个人,一个个村寨,一件件事。这种霸得蛮的精神,也只有我们湖南蛮子纪红建做得到。下了这种功夫,不愁得不到潮水般的好评。
林乐伦:作为湖南文艺界的负责人之一,你对推动湖南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有些什么思考?
夏义生:省委省政府发出了重振文艺湘军雄风的动员令。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全省文艺界共同努力,希望在中国文艺方阵中永远有一支最优秀的队伍——文艺湘军。现阶段,文艺湘军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么响亮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把湖南打造成优秀文艺创作高地。不管是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舞蹈,还是电影、电视、摄影、杂技、曲艺、民间文艺等,所有的门类,都应该有优秀的作品来支撑文艺湘军在全国的地位。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没有一个庞大的文艺人才群体,是不敢想像的。这就要求各文艺门类都应该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实施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就是要造就一批优秀的文艺家。对于老文艺家,要发挥他们在创作上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对于中年文艺家,要珍视他们难得的创作喷发期;对于青年文艺家,要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尽快成为文艺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
林乐伦:作为省文联负责人,您对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提几点希望和要求,好吗?
夏义生:我觉得基层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接地气,且接触的工作对象的面是最宽的,基层文艺工作者接触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文艺爱好者。我们要把接地气这个优势转变为工作上的优势,那就是真正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我们服务的对象上,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需。要始终不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天职。要坚持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的要求。我们文联组织就得承担起这个职责,集中精力,集中资源,推动出作品,出优秀作品,出留得下、叫得响、传得开的作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回报人民。当然,这两者也是互相联系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不是在空中楼阁产生的,它源自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需求,是文艺工作者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林乐伦采访夏义生(右)
编者按
始终不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天职,这是重振文艺湘军雄风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日前,在《雁鸣故里》一书编辑完毕之际,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林乐伦就如何重振文艺湘军雄风等问题,采访了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秘书长夏义生先生。本报现将其对话整理刊载,以飨读者。
王船山故居
纪红建所著的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夏义生的评论集《消费时代的文化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