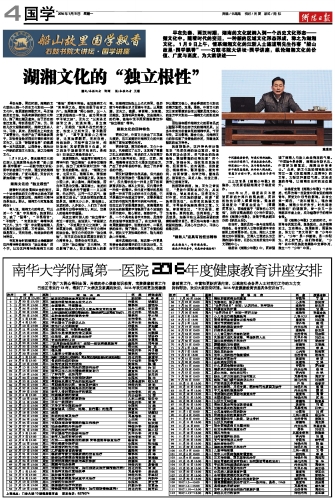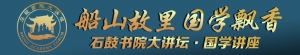■文/本报记者 许珂 图/本报记者 王翟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就纳入到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像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到了南北朝及唐宋,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先后产生了理学鼻祖周子,主张经世致用而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夫之,以及“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一系列思想家,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1月9日上午,情系湖湘文化的江浙人士施道明先生作客“船山故里·国学飘香”——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第三十六讲,通过讲述湖湘文化的价值、广度与高度,来告诉大家如何做一名“湖湘” 人。
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必然会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出现,湖湘文化精神亦是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究竟缘起何处?
有人说,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施道明认为,除了“强悍”、“ 不畏艰苦”、“ 不怕死”、“ 尚武任侠”等精神风气之外,这个“蛮”字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特征。
辛亥革命时的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征概括为“独立根性”四个字,认为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根性”即根本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之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施道明表示,钱基博对湖湘文化精神中的“独立根性”也曾作过概括分析,指出了地理环境对这种“根性”形成的影响。他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这段话简扼的意思就是说,湖南水少山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人多地少,人们为了生活必须得付出艰辛和努力。所以,这里人的性格非常倔强。
冯友兰曾对楚人的“独立精神”有过一番议论,他说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并举屈原为例,说明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独立性。楚文化中的这种“独立根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屈原这样的文化精英身上,而是处处可见的。
这种“独立根性”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楚人,而且通过楚人的影响,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至今不息。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直到毛泽东等等,这些湖湘人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根性”精神。
湖湘文化的四种特色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
而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以倔强不羁为生存方式的湖湘民风,以务本求实为价值体现的湖湘学风,千百年来,互为影响,融合化生,为湖湘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酿造其强烈的地方特色。
施道明表示,这种特色突出表现在“无须依傍的独立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四个方面。若细分来,则体现在民族自尊、报国情怀、志向高远、自信豪迈、牺牲精神、鄙弃庸俗、崇尚学问、治国智慧、治军方略、廉洁品质、勤苦毅力、坚贞人格、处世之道、读书之道等方面。
施道明举例道,如,王夫之曾说过,“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这是王夫之对中国,对汉族的期望,所谓“固族类而无忧”,也即使民族强大坚固,不再被异族摧残侵犯之意。又如,曾国藩说过,“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意思就是,如果不能以圣贤的圣贤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便只能与禽兽一般为欲望所控制。只关心付出多少,不关心结果怎样。
“湖湘人”应具有的担当精神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
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
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
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
留慈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
……
以上这首是《湖南少年歌》的摘抄,为民国初期湖南才子杨度所作。
1903年10月,杨度在日本邂逅同样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同样的抱负让两人惺惺相惜。梁启超视杨度为“谭复生复生”(谭嗣同再世),而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为附议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便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
在当时,激进思想一般与地域观念相结合,各省爱国人士都在强调本省在救国上的重要作用。比如,湖北人士称湖北为中国腹地,云南人士表述认为云南存则中国存,江苏认为其区域为中国文明的中心。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同样强调了湖南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此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写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力挺这种豪迈气度。这些名篇的传唱,让湖南在当时的地位飙升。
在杨度发表《湖南少年歌》十多年后,毛泽东等一批改变中国命运的湖湘青年,深受文中呼号的影响。在省立第一师范,“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的诵读声,曾一次又一次响起在学堂上空,成为勉励学子的精神食粮。
而《湖南少年歌》之后的时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激荡起伏,众多湖南志士,立在潮头,施展救国、图强抱负,努力让“老大帝国”变“少年中国”。“少年”是一种隐喻,是一种阳光、向上的气质。他们都希望,“少年”在中华民族改变颓势中发挥作用,建立一个“少年”中国。
施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