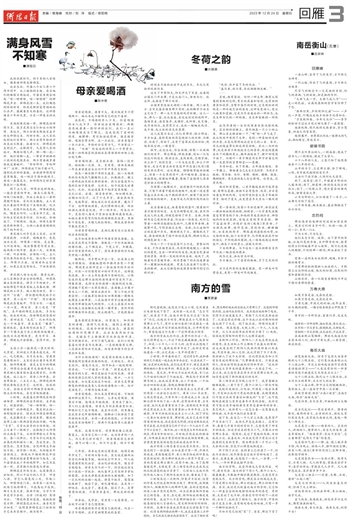■谭旭日
我的孩提时代,村子里的人家嫁女,都要请师傅来弹棉花。
我出生后,外婆八个女儿有六个待字闺中。从三姨妈到幺姨,每当她们的婚嫁日期临近,外婆家里便会响起“嘭—嚓嚓嚓,嘭—嚓嚓嚓”的弹棉花声音。弹棉花佬一来,我们都感到特别新奇。特别是弹弦富有韵味的打击声,蕴藏着巨大的喜悦。这种情绪在少年时光里,亦是一种莫名的欢娱。
东湖到黄泥铺一带,弹棉花的师傅不多,很多是周边安仁和永兴的师傅。再远点,偶尔会请来衡南宝盖乡的大师傅过来。约好日期,主人家就赶到他们家帮忙,偶尔会有年轻的学徒在后头跟着,挑着行头。弹棉花的走村过户,过桥拐弯,凡是有人家的地方,都要吆喝几声:弹—棉—花—啰。他们前脚一走,一帮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就尾随其后。偶尔有婆姨拿着鞋底追着喊叫:“等哈即啰,等哈即啰!”这样,师傅便放下担子歇口气。遇到礼性好的婆姨,会邀请师傅到堂屋里做客,端一碗浮子酒和酸辣子,再端一盘落花生,和师傅约定好家里要添打一张棉被。
到了主人家,师傅会选好场地,一般在堂屋的中央。搬来几张高凳,四块门板铺垫,然后上面盖上一层新薄膜作案板。家伙还没操起,主人家就忙着招呼师傅坐下来喝杯酒,吃点果点,还随个红包礼钱。师傅收到礼钱,嘴里乐呵呵,心里乐开了花,连忙给主家说些吉利话。比如说:添福添丁,丁财两旺。随后,师傅又张罗徒弟拆卸弹弓,七拼八凑磨磨蹭蹭就到了晌午时光。
黄泥铺人叫手艺匠工来家,必须热情款待。六碗荤,鸡鸭鱼肉,色色油水光亮。师傅第一顿饭,是主餐,又叫进场饭。随后餐餐有肉有豆腐,起码要六碗齐整。最后一天,还要做一顿,叫出场饭。出场饭一吃,主人家就要用红纸包个包,把工钱一并随上。师傅不点数,进场前和主家讲好,如果主家没有给足,下回再请就难。
黄泥铺人嫁女也好,娶亲也好,主人家都会拿出全新的棉花。师傅根据主家的要求,弹多少斤的被子,开始把棉苞平铺在案板上准备就绪。弹棉花的工序多,做工颇为讲究。第一道叫“打散”。将结团的棉花球子打散开。第二道叫“平铺”。用打散的棉花放在案板中,作长方形。一般是一米八宽,两米长。第三道是“布线”,在平铺的棉花上张线,多为红线,结成丝网状,保持棉花的坚固耐用。第四道是“走花”。比如用红线走一个双喜字。第五道是“碾磨”,张好线后,基本雏形就出来了。师傅拿一个圆木盘子在上面使劲地碾压,把线头压进棉绒里,更为牢实。再者,棉被也不会膨胀,显得平坦、整洁。
五道工序一般要花一整天时间。天黑前,第四道工序基本能完成。所以,吃完晚饭,当月光来临,堂屋里亮着煤油灯,主家还会打着手电筒照着,陪师傅碾磨。若是主家打的棉被多,师傅还会赶着月光再铺开起工。黄泥铺人娶亲嫁女喜欢图吉利,打棉花被,选三选六。前者三阳开泰,后者带陆合。三五天工夫,弹棉花的师傅就要做完这手艺。这时候,临近的人家,会把自家的旧棉胎拿来翻新,借主家的场地,在自家做饭谢客。
小时候,我最喜欢弹棉花匠的劳动场景。弹棉花的右手持槌,左手把弓,槌落弦绷,“嘭—嚓嚓嚓,嘭—嚓嚓嚓”的弹棉花声,像是村庄的一曲舒缓的音乐。特别是师傅在弹棉花前,先在腰间系一条阔皮带,腰后的皮带上插一根两指宽的粗竹鞭,叫做“弓背”,弓背从后背的头顶举起,顶上又垂下一根绳子,这根绳子从师傅的正面悬下来,正好将那张大弓吊起来。每一次弹打,弓背与手之间表现出高度的和谐与一致。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重忽轻,全凭师傅左手按住弓把,右手持一木槌,木槌敲在牛筋弦线上。弦线从平铺的棉花中经过,棉花就轻姿曼舞地纷飞起来。这个姿势在我少年的视野中,如艺术表演一样,具有强烈的质感与律动。
弹棉花是件体力活,也需要慢工出细活,所以干这行的人不多。听老人讲,学艺人要夏练三伏,冬做三九。师傅领进门后,徒弟第一道功夫就练习把持棉弓,不能高也不能低,棉弓又长又重,很难平衡,不学个半年是学不会的。古诗《竹枝词》有诗为证:“棉花街里白漫漫,谁把孤弦竟日弹。弹到落花流水处,满身风雪不知寒。”说明靠弹棉花这门祖传的手艺来养家糊口,颇为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