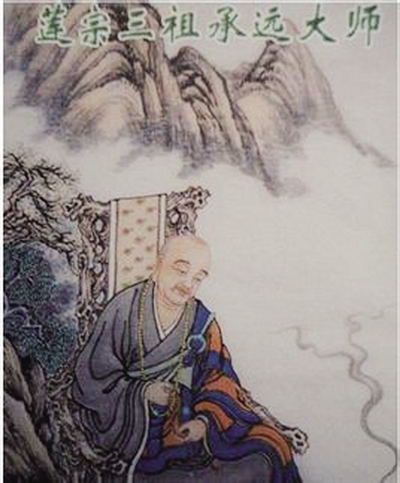
承远大师像。(资料图)
■廖和平
承远(712年—802年),南岳弥陀台始创者。唐汉州绵竹(今四川德阳)人,俗姓谢。师承净土宗,是净土宗来南岳弘法的第一位僧人。年少出家,初在资州智诜的弟子处寂门学习禅法,密悟其道。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至荆州当阳玉泉寺受学于惠真禅师,正式剃度出家。不久,受惠真禅师之命,南来衡岳,孤身单影居住南岳紫霄峰(又名驾鹤峰)岩石之下。在南岳从衡山中院通相禅师受具足戒,后去广州随慈愍(即惠日和尚)学习净土宗的经典教义。此时,净土宗已分为三个支派:慧远派、善导派、慈愍派。承远成为净土宗慈愍派的主要传人。唐天宝(742年—755年)初,承远回归南岳,居山之西南岩卞,披茅以居。他持戒极严,苦行修持,除研读教义,劝化他人外,总是合掌盘坐,一心专念弥陀,非力竭不休,故称“弥陀和尚”。
承远弘法南岳凡六十年,苦节真修,老而弥笃,王公商贾布施所得,都用于法宇建设和施舍贫乏者。承远主张立般舟行,往生净土。所谓般舟行,意为常行道,七日或九十日不断的修持;谓至心念弥陀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净念相继更妙,故俗称“念佛宗”。因该宗教义不深奥,也无烦琐经义,极易为普通信士所接受。以致“南极海裔,北至幽都”鹜趋南岳向承远求教。后世尊承远为“净土宗三祖”。承远卒于贞元十八年(802年)七月十九日,世寿91岁,为僧56年。人们为了纪念他,特为他修了一座庙,唐德宗皇帝赐名为“弥陀寺。”
他逝世后,时永州司马柳宗元为之作《南岳弥陀和尚碑》,并亲自书石。原碑藏弥陀寺,唐武宗(845年)排除佛教时,转藏相距30华里远的南岳祝融峰上封寺,南宋时为潭州运帅曹彦约取去,不存。
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尽管心情郁闷,仍尽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他强调佛教的伦理观,主张孝敬父母,并提出佛经中有《大方便佛报恩》等十篇宣扬孝道的经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学说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结合,又把儒家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的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合的表现。
814年,柳宗元撰《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达是道者,惟大明师。师姓欧阳氏,号曰惠开。唐开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宝十一载始为浮图,大历十一年始登坛为大律师,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怀信、道嵩、尼无染等,命高道僧灵屿为行状,列其行事,愿刊之兹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师先因官世家潭州,为大族,有勋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图也。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大明恐焉。于是从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洎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隐显。后学以不惑,来求以有得。广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二十一人,师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七人,师应其数。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匜、奉杖屦,为侍者数百;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趾下,碑在塔东。其辞曰:
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量,垂裕无际。诏尊硕德,威仪有继。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辞,弥亿千岁。
惠开(725年—797年),即大明和尚,俗姓欧阳,家为潭州大姓,是为南岳一代宗师。童年,梦大人缟冠素舄来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尔也。”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剃度出家,受具足戒。代宗李豫广德二年(764年)立大明寺于衡山中山沟,获选任大明寺主僧。乾元元年(758年)诏衡山立毗尼藏,选讲律僧七人,应其数。大历十一年(776年)始登坛为大律师,主戒事22年,受戒弟子数万人。宰相齐映、李泌、赵憬,尚书曹王皋、裴胄,侍郎令狐峘等,或师或友,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贞元十三年(797年)卒。将终,夜有光明,笙磬之音,众咸闻见。弟子有怀信、道嵩、尼(女弟子)无染等。
中唐时,衡岳戒法的地位很高,成为天下律学中心之一。七大德中,为首的是云峰法证,般舟日悟、希操、惠开都是当世律宗大德。云峰法证临坛五十年,度众五万,大弟子三千余人;般舟日悟“度比丘众,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总数亦有三万七千多人;希操度众二十六会,按照每次千人的规模,有二万六千多人;惠开登坛二十余载,“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单是他们四位高僧,所度之众就有十几万人。
柳宗元讲:“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家的礼、仁义与释家的律、定慧,都有自身的内容规范,是它们各自思想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吸取各自有益的养分,有其相近的同构形式。大明寺律僧惠开“究戒律”“通经教”“大法以立”“奥义以修”。佛门里的“衣服器用”“言语行止”都纳入严明的纲纪法则之中,以保持佛门的清净庄严。惠开恪守戒律,“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者,灏灏焉无以加也。”律、礼所要求的规矩成为释家、儒家所共同希冀塑造的人格典范。惠开以其身体力行的人格美德成了儒家所看重的僧人也就不奇怪了。佛教“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其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研习、修持戒律,无非也是执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具体行为约定。“法不周施,禅不大行,而律存焉”,法、禅都有它们自身的弱点,于是律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它成为佛教存在的一个重要的行为规范的标尺,没有戒律的约束,出家人与世俗人也就谈不上根本的区别。
815年,柳宗元撰《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并序)
衡山中院大律师,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诫盈,奉公之遗事,愿铭塔石。公昝姓,凡去儒为释者三十一祀,掌律度众者二十六会。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尝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公、瓒公(懒残),言未尝形,遇公而叹息,推以护法。是以建功之始,则震雷大风示其兆;没迹之际,则陨星黑祲,告其期。斯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与物大同,终始无争,受学之众,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贞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干、惟正、惠常、诫盈,皆闻人。呜呼!始终哉。为之铭曰:
首有承兮卒有传,革大讹兮持法权。众之至兮志益虔,雷发兆兮功已宣。
星告妖兮寿不延,灵变化兮迎大仙。砻兹石兮垂万年,世有坏兮德无迁。
希操(732年—788年),俗姓昝,原为儒生,籍贯不详。唐代僧人。出家后,住衡山中院掌律度众,凡26年。一生度人无数,其弟子中有不少是禅宗大师,因此他与禅宗有不解之缘。柳宗元在《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上说:“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当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又说:“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贞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干、惟正、惠常、诫盈,皆闻人。”足以说明希操在南岳弘扬律宗影响之大。柳宗元对希操复正南尼戒法,再成衡岳佛寺之举十分推崇。
据《南岳志》记载,希操的弟子诫盈与韩愈为方外交,韩愈有《别盈上人》诗云:“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率俗来何时?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反映了诫盈上人隐居深山,超尘脱俗的志向。
柳宗元的这些碑文铭辞,所叙人物全是闻名遐迩的高僧大德,大多是受逝世和尚的弟子请求而写作的,但绝不作“应酬之作”,每一篇碑文都是一篇极佳的散文。较好地概述了他们一生的行迹,以及他们不辞辛苦,勤奋专心钻研佛经,坚守节操,渡己渡人,终于有了很深的造诣,在不同的时期成为一代名僧。
这些碑文真实再现了盛唐时期的南岳佛教生态,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史料性和思想性,是后人研究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