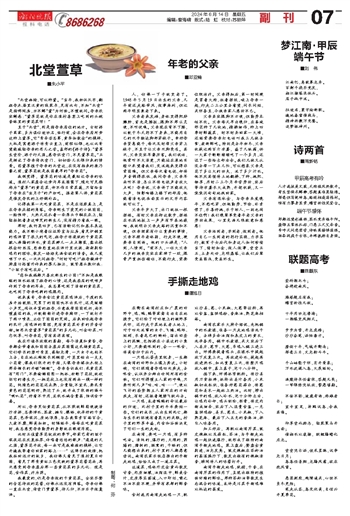■朱小平
“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当年,我初识汉字,翻祖母木屉里泛黄的线装书,见有此句,不知“北堂”是指哪间房,亦不解“萱”为何物。不懂就问。母亲欣然解惑:“萱草花就是你在渔村喜宴上吃到的头碗香钵里的黄花菜呀!”
至于“北堂”,则是指母亲居住的地方。古时游子离家,多为谋仕途功名,临行前,会在母亲居所旁边种上萱草。它“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的模样,大抵是寓意游子将青云直上,前程似锦,也以此寄望能减轻母亲的思儿之苦。孟郊的《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门,不见萱草花。”正是描述了母亲倚扶堂门、切切盼儿衣锦归来的情景。因萱草植于母亲的北堂边,在没有舶来的康乃馨之前,萱草花就是我国最早的“母亲花”。
我倒觉得,萱草花的味道是最贴近母亲的味道。渔村人家屋舍近旁沟岸或园篱下,随处可见雅称为“萱草”的黄花菜,却不作日常菜蔬,只留给当了母亲在“坐月子”的产妇吃。据老辈人讲,黄花菜是催发母乳的上好调补品。
记得我第一次吃黄花菜,不是在酒席桌上,是在母亲床榻的角落。母亲刚生下爱哭的小妹囡囡,一脸憔悴,大热天还扎着一条厚头巾躺在床上,轻轻拍抚着身边啼哭的新生儿,没有精力看我一眼。
那时,我约莫四岁,已有清晰记忆和基本表达能力。我不断小跑着往返卧室与灶房,看见炉锅里的鸡汤冒了很久的气泡,祖母才将浸软的干黄花菜撒入沸腾的汤水,黄花菜瓣儿一点点膨裂,露出根根金针丝蕊,忽曲忽直地在汤汁里欢跳,渐渐剔除鸡肉的腥味,散发一缕缕充满食欲的清香。我几度咽下口水,一次次问祖母:“何时可吃?”祖母凝神于厨屋竹格窗外传来的婴儿抽泣,皱紧眉头敷衍我:“小孩子有吃在后。”
“您和我妈都只喜欢新生的小囡!”不知是我眼眶的泪水淋湿了祖母的心情,还是我委屈的哽咽声传到了母亲的耳朵,我总算吃到了清甜的黄花菜,也吃到了母亲吃剩的鸡腿肉。
说来真奇,母亲食过黄花菜鸡汤后,干瘦的乳房开始鼓胀,哭累了的囡囡吮不出乳汁,还是继续小声哭。阅识丰富的祖母,示意我帮囡囡吸奶,尚不懂羞涩的我,兴致勃勃扑进母亲胸怀,一下就打开了两口喷泉,止住了囡囡的哭闹。后来回味起母亲的乳汁,有鸡汤的荤腥,更有黄花菜朴素的芳香甘甜。细思北堂萱草“黄花菜”的多元化,叫金针菜、叫忘忧草、叫母亲花,皆有其源其理。
我在外读书放假的暑期,每个清晨和黄昏,母亲都会带着我和囡囡去屋后菜园篱边采摘黄花菜。它们修长的碧叶青茎,柔韧光滑,一只虫子也粘不上去,自在地从稀疏长到稠密,叶茎里钻出一支支小花箭,像我们张开的手指,又像母亲嫁妆木柜上那条椭长的开锁“铜销”。母亲告诉我们:采黄花菜有“窍门”,不要偷懒囫囵一把抓,折断了花枝,就破坏它的潜生力,一柄花枝上也没有两朵一模一样的花。纯绿色的花苞还未熟,分量轻,不宜采,要采青黄色的花苞刚好,熟过了头,就开成了张扬的漏斗“喇叭花”,好看不中用,且秋水碱含量高,怕误食中毒。
所以,母亲烹饪黄花菜,从不敢就鲜图便捷清炒凉拌,总要焯水、蒸煮、摊匀、曝晒,收存好的干黄花菜,色泽深沉,质地淳厚,与各类荤素百搭百合,久煮不糜,鲜美如初。时隔经年,每每在吃黄花菜时,我总感觉母亲勤劳的身影就在眼前浮现。
此时正值萱草花绽放的季节。邻家艺考的孩子深夜还在反复拉琴,伴唱着悠悠的歌声:“遥遥的天之涯,萱草花开放,每一朵可是我牵挂的模样,让它开遍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这绵长的旋律,把我拉回远方的故乡,我仿佛又看见了渔村夏日田园,看见了那青黄红三色交映的萱草花蕾花朵,再次感受到母亲屋后那一垄黄花菜的多元化:观是花,食作菜,疗为药。
我最爱的,仍是母亲做的干黄花菜。全然齐整的含苞待放的花蕾,仿佛永远没有凋落。母亲仿佛一直在北堂,倚堂门赏萱草,待儿归,不亦乐乎做羹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