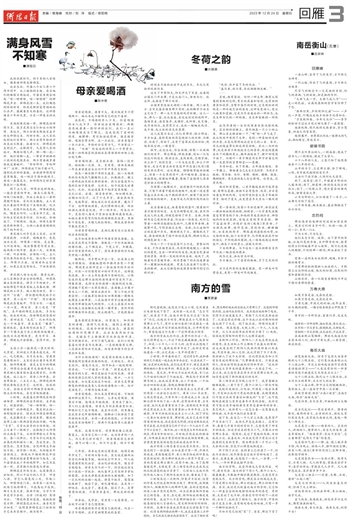■陈中奇
母亲爱喝酒,酒量不大,每次饭前多少得喝两口。她从来也不掩饰自己的这个喜好。
在农村,不喝酒的男人少见,但爱喝酒的女人也不多。母亲说出爱喝酒时,两眼晶亮地看着一脸惊讶的我们,我们一直以为她喝酒是为了解乏,没成想到了爱好的程度。她解释:有句俗话说得好,酒是粮食精,喝酒长骨力啊。这一点我信,母亲身高才一米六出头,年轻时壮实有力气,干活赛过一条垄,“双抢”时妥妥的顶得上一个男劳力,挑着一担堆满筐的湿稻谷在滑溜溜的田埂上能打起飞脚。
母亲喝的酒,是自酿米酒。每隔一段时间,她就酿一次酒。米,家里有,酒曲是她前一年在房前屋后采淡竹叶等中草药自制的。
找来一面洗擦干净的大簸箕,把一大锅煮熟的白米饭热气腾腾倒上去,扒散摊凉,撒上一层研成粉末的淡黄的酒曲,拌匀后装进半人高的瓦坛子里发酵。大热天,坛子就露天放着也行,天冷,就放进屋角干稻草窝里保暖。三五天以后,出酒,酒清香甘甜,初如稀米汤,后稠如白乳汁,过了十天半月,酒会很快变老,发酸带涩,糟也由乳白变成麻黄,瘪化了下去。这种原始酒浆,我们惯称湖之酒。新出的湖之酒很受欢迎,冲一碗井水,用来打口干,是农村人每天干重活后佐餐的最佳饮品,如把泛着白色絮化饭粒的酒糟烧至滚烫,里面卧个荷包蛋,点缀几枚红枸杞,那就成营养的早餐或宵夜了。
而母亲常喝的酒,是湖之酒变老以后再蒸制出来的烧酒。
也不知道母亲从哪个邻居家借来酒甑,反正我家没有这个器物。酒甑是一个杉木板编成的圆形桶,上下都没底,下宽上窄,齐腿高,估计村里借用的人多了,原本黄澄澄的杉木板蒸熏起一层黝黑。
甑侧放,用手臂从中空一穿,扛在肩上倒也方便搬运。酒甑板壁的半腰间凿有一个圆洞,那洞里正好伸进去一条接酒用的半剖竹筒,竹筒一头仍留有封口的竹节内片,这样能兜住酒,另一头上吊坠着两个茶树坨坨,以便坠成斜度让那头接到的酒顺着竹筒自然下流。预备蒸酒,先将变老的酒糟一股脑倒进大锅,用酒甑下宽的一头罩住锅沿,在酒甑上方圆口再坐上一只锅,锅里注满凉水。有三个地方需要密封:一是甑罩住锅沿处四周要撒一圈糠末或围塞上破布条,二是接酒竹筒穿过甑的圆洞处要用布堵住漏气的缝隙,三是上层装凉水的锅与甑上沿接触处也要裹一圈布条,密封用的材料都要用水浇湿,防止跑酒气,才能提高出酒率。
基本原理是蒸馏法,灶里烧火,加热锅里的酒糟,酒精气化蒸发,遇到上面装凉水的锅底,迅速冷却凝结成液态,滴落到接酒的竹筒槽子里,流出来再用坛子接住。关键在于上面锅里凉水会逐渐升温,需不断换凉水,才利于酒气凝结。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母亲在冬天熬酒,一是烧硬柴有火烤,二是换水有热水可洗澡,而母亲却要不停去井里担水来换。
为什么称烧酒呢?就是因为要烧火熬制,喝酒能明显喝出烧柴的味道。头酒较淡,渐次变浓烈,酒尾子也淡,但中和在一起就刚好。母亲说:“一斤粮食一斤酒。”村里也有专门酿酒卖的人家,确实是按这个比例兑换。母亲熬的烧酒总比别人家的度数高,辣口,一点火就能着,如太寡淡就没个味道。母亲总是带着鄙夷的神情说某某人家的烧酒像水一样,估计是酒尾子,只够用来做米醋。
母亲爱喝酒,但从来没有醉过酒,可她的酒却醉过很多人。年轻时,父亲也爱喝酒,酒量还不错,能喝大半瓶烧酒。家里来了客人,男人们上桌喝酒,母亲大多仍在厨房里忙活,即便忙完了也不喝酒。我至今记得,村里屠夫在我家杀完年猪喝醉酒,抬脚出门就摔进了屋外面的水沟里,弄得一身泥的尴尬;小学老师来我家家访喝醉了,得两个同桌的男人扶着才能离开。
现在,我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备上烧酒。餐桌上,我为自己倒一小杯,也为母亲倒一点儿,而父亲已经不喝了。母亲喝酒前总告诉我,酒可以喝一点,但不可过量,绝不可喝醉。
几年前,母亲也自制过葡萄酒。起因是她年岁大了,不时闹头昏头痛,医生说是脑部血管老化加堵塞导致,她四处打听单方,听人说葡萄酒有软化血管、活血化淤的效用,便自学自制起来。母亲大字不识一个,但学起这些生活小技能一学就会。她从集市上买来好多紫红的葡萄,去皮洗净装进泡酒的大玻璃罐,加了一定比例的冰糖一起泡,静置个把月,葡萄酒就做好了。她尝了尝,咂巴着嘴说:真是另一种味道。我也尝了,酒是酒,轻淡了点,是带葡萄味的酒。只要母亲喜欢,那就是好的酒了。
母亲说,先学会,家里有一大篷葡萄,以后就可以摘了自己慢慢做。
母亲喝酒的哲学是喝自己酿的酒,而且一辈子不喝醉,这才是她嘴里说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