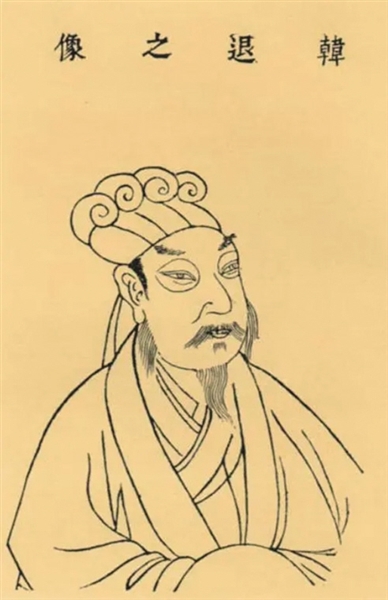
韩愈 像

杜甫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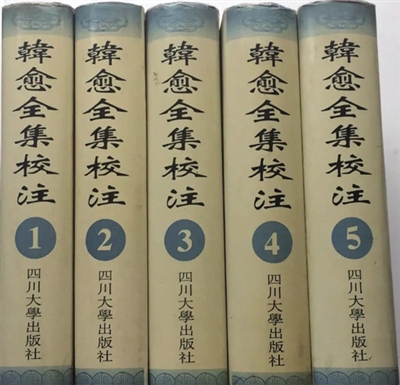
■廖和平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愈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系唐代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据考,韩愈一生多次经过湖湘。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任监察御史时,因关中大旱,上疏请求减免赋税,反对宫市,得罪权贵,被贬为3000里外的广东连州阳山县令。
永贞元年(805年),韩愈遇赦,离开阳山,在湖南郴州待命三月,至八月始调任湖北江陵府法曹参军。他于是访郴州,探耒阳,客衡州,谒南岳。
衡阳,应该是韩愈坎坷而灿烂人生中最美丽的遇见!笔者通过《韩愈全集》,找到他在衡阳的主要作品,有《题杜工部坟》《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谒衡岳遂宿岳寺题门楼》《岣嵝山神禹碑》《别盈上人》《送廖道士序》等。
耒阳凭吊诗圣杜甫
韩愈是杜甫的超级粉丝,虽然,杜甫去世的那年,韩愈才两岁,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但是,韩愈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态度,却非常热情炽烈。据说,韩愈还经常梦见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永贞元年(805年)春,韩愈遇赦,在湖南郴州待命期间,他结交当地名流,访古寻真。路过耒阳县城时,弃舟登岸,由东门入城,停歇之后,出北门寻到杜甫墓前,有凭吊《题杜工部坟》诗一首:
何人凿开混沌壳,二气由来有清浊。
孕其清者为圣贤,钟其浊者成愚朴。
英豪虽没名犹嘉,不肖虚死如蓬麻。
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芽。
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
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
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
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
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
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
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
召朋特地踏烟雾,路入溪村数百步。
招手借问骑牛儿,牧儿指我祠堂路。
入门古屋三四间,草茅缘砌生无数。
寒竹珊珊摇晚风,野蔓层层缠庭户。
升堂再拜心恻然,心欲虔启不成语。
一堆空土烟芜里,虚使诗人叹悲起。
怨声千古寄西风,寒骨一夜沉秋水。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子美当日称才贤,聂侯见待诚非喜。
洎乎圣意再搜求,奸臣以此欺天子。
浊月走入千丈波,忠谏便沉汨罗底。
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贤所归同一水。
过客留诗千百人,佳词绣句虚相美。
坟空饫死已传闻,千古丑声竟谁洗?
明时好古疾恶人,应以我意知终始。
《题杜工部坟》用了大量的笔墨,对杜甫的才情推崇备至。
韩愈此诗,为杜甫卒葬耒阳的重要证据。当时,距杜甫逝世仅30多年,当年目击杜甫卒、墓者大有人在。韩愈凭吊杜陵时,耒阳县令亲自引路,按旧时官场上的惯例,内官左迁,外官奉若神明,倘若这是假墓,县官敢引韩愈去祭拜?“牧童指我祠堂路”“入门古屋三四间”,从该诗中可发现,杜甫去世后的30年里,当地人已在墓地建了祠堂,不过很简陋,只有三四间老屋,远没有后来杜陵书院的壮观。
据《耒阳县志》记载:“祠堂初建成后,县令申详上宪,配有供俸常额,明及明前额编门子一人看守,清门子易为僧。每岁孟春三日至孟秋三日由县官率师生行释奠礼。清孟春三日易为三月三日,秋奠如旧。”
韩愈对杜甫被牛肉撑死之事表示怀疑,认为杜甫实同屈原、李白一样,都是淹死的,牛肉撑死之说,是聂县令的谎话,目的是搪塞天子搜求杜甫的遗体。韩愈的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新、旧《唐书·杜甫传》均采此说。
可以说,韩愈是杜甫去世后第一个对他作出崇高评价的人。有资料显示,韩愈此行还到耒阳汉代名臣张良隐居过的“张良洞”瞻仰,题写了“还我本来面目”六个字。
石鼓山留下千古绝唱
是年八月,韩愈正式接到任湖北江陵府法曹参军的调令。他乘舟向北,慕名来到衡阳石鼓山。韩愈的到来,对于衡阳的文化界无疑是件大事,时任衡州刺史的邹君(儒立)欢喜异常,设宴于石鼓山上的合江亭,盛情款待。
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四年(787年—791年),期间,在石鼓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
宾主尽欢,心情大好的韩愈站在“一郡之佳处”的石鼓山上合江亭,面对宽阔的江面和奔流不息的江水,不由得胸怀开阔,心旷神怡,感慨万千,写下千古绝唱《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
维昔经营初,邦君实王佐。翦林迁神祠,买地费家货。
梁栋宏可爱,结构丽匪过。伊人去轩腾,兹宇遂颓挫。
老郎来何暮,高唱久乃和。树兰盈九畹,栽竹逾万棵。
长绠汲沧浪,幽蹊下坎坷。波涛夜俯听,云树朝对卧。
初如遗宦情,终乃最郡课。人生诚无几,事往悲岂奈。
萧条绵岁时,契阔继庸懦。胜事谁复论,丑声日已播。
中丞黜凶邪,天子闵穷饿。君侯至之初,闾里自相贺。
淹滞乐闲旷,勤苦劝慵惰。为余扫尘阶,命乐醉众座。
穷秋感平分,新月怜半破。愿书岩上石,勿使泥尘涴。
韩愈的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吟咏石鼓山合江亭的诗,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尤其是“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而合江亭亦因此又被称为“绿净阁”。“波涛夜俯仰,云树朝对卧”是石鼓山的真实写照。
王夫之称:“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则裴度也、李绅也、韩愈也”。后来,石鼓书院名列“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两受皇封,人才辈出,则韩愈功莫大焉!
韩愈还来到衡阳城北木居士庙(耒阳也有木居士庙),木居士是对木雕神像的戏称。陈有期先生在《嘉靖衡州府志》校注中云,衡阳木居士或指湖北襄阳寓衡名居士庞蕴。韩愈有感而作《题木居士二首》云: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为神讵比沟中断,遇赏还同爨下馀。
朽蠹不胜刀锯力,匠人虽巧欲何如?
韩愈衡山精诚开云
泛舟湘江,岂能错过天下闻名的南岳? 他在《祭河南张员外文》云:“委舟湘流,往观南岳。”
韩愈是怀着对南岳衡山的久仰和敬重之心登顶的。时值秋天,南岳古镇一带天空浓云密布,阴雨连绵,不仅登不了山,连秀丽的山峰也叫云遮住了。碰上这种坏天气,韩愈大失所望。他本不大信神,夜宿岳庙,便叫童仆拿来一把香,点燃插到岳神前,自己则默默地祷告起来,祈求岳神驱开云雾,让他登山游览,了却多年心愿。说来也怪,韩愈烧香祷告后,好像岳神真的被他的虔诚所感动,顿时雨止云开,露出了一轮朗朗秋月,将南岳诸峰照得清晰可见。韩愈喜出望外,次日赶忙登山。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公之诚,能开衡山之云”。韩愈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中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诗云: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
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
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
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
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
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
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
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
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
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
夜投佛寺上高阁,星月掩映云朦胧。
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
诗句首先总叙衡山的地位声望。《礼记·王制》说,天子以三公之礼祭五岳,唐时五岳之神都封王号,衡岳神封“司天王”,为众山之尊;衡山威镇炎方,为南天之雄峰,云封雾绕,高不可攀。这是韩愈心目中的衡山,起笔高古,不落凡俗。
韩愈乘兴而来,适逢秋雨,连日阴晦,原以为此行看不到衡山真面目了。及至上山,忽然云开雨霁,众峰尽出,心情也随之像天宇一样开朗。笔势排宕,开阖多变。以天朗气清的秋空为背景,衬托着远近诸峰的突兀环立。景象阔大,气势宏伟。“潜心默祷若有应”,“若”字含有山灵似有似无、韩愈似信未信之意,颇堪回味。“须臾静扫众峰出”,“静扫”,指风吹云散。云过无声,故曰“静”,云去无迹,故曰“扫”。南岳七十二峰,芙蓉、紫盖、天柱、石廪、祝融五峰为最高。众峰“突兀撑青空”是全景,“紫盖”二句连写四峰不同形状,是特写,虚实相生,有动有静,表现了衡山的雄奇壮丽。
韩愈拜谒岳庙。寺外松柏夹道,一径登山;寺内粉墙丹柱,图画灿烂。从衡岳庙修饰之新,可见香火之盛。但韩愈拜祭是为了在神前“明其衷”,即申诉内心的郁抑,表明自己尽管遭到贬谪而不变初衷。庙令老人以为他一心“求福”,倒掷杯珓(一种占卜工具),为卜富贵,一味恭维。在祭神的恭敬肃穆的气氛中插入了诙谐之笔,别具情趣。“识神意”“能鞠躬”二句,极其揶揄。所谓“睢盱侦伺能鞠躬”,实际上是说他善觇人意,善于逢迎。“窜逐”四句,即韩愈“明衷”之语,说得婉转而又倔强。占卜“最吉”,但他无所动心,谢绝了庙令的好意。韩愈远贬南方,是因为直谏而“为幸臣(指京兆尹李实)所谗”。因此他充满自信,无求于神。这首诗题于衡岳寺的门楼上,也似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向衡岳山神表明心迹。
当夜他就宿在寺庙里。夜宿高阁,星月隐约,一枕酣睡,醒时已杲杲日出。“猿鸣钟动不知曙”,昨夕的神前卜吉,早已忘怀,虽是贬谪之身,但心怀坦然,睡得安稳,猿鸣钟动都闹不醒他。
全诗实为一篇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的记游佳作。
为纪念韩愈游岳胜事,人们将岳庙外的一座门楼改名为“开云楼”。1936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高台寺下修建一座花岗石八角亭,命名叫“开云亭”。
“韩愈开云”的美谈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开云亭、开云岭、开云镇、开云中学等与“开云”有关的名字也都是因他而来。
在华夏文明史上,南岳“禹王碑”是个神奇的存在,古人对其极致推崇。“禹王碑”最早的文字记载,一般认为,是见于罗含(历西晋和东晋两朝)所写的《湘中记》:“岣嵝山(古指衡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
此行,韩愈亲自到南岳衡山寻找“禹王碑”,但是经多方努力,却没有找到。失望之下,他作了首《岣嵝山神禹碑》诗,悻悻而归: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蝌蚪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
森森绿树猿猱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