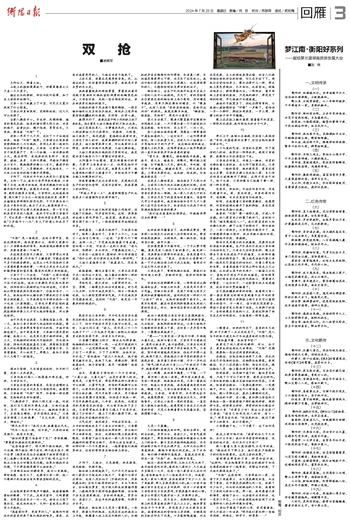■凌拥军
1
太阳似火,烤着大地。
山坡上的植物蔫蔫欲干,好像离燎原之火只差一个火星子。
塘边近水的柳树,却依旧枝叶苍翠,知了在上面拼命地嘶叫。
父亲一出门就戴上了斗笠,可见炎炎夏日热到了什么程度。
父亲从田里回来时,笑眯眯地说:过几天可以收割了。
全家人都很开心。年成好,风调雨顺,塘里的鱼没发病,栏里的猪长得又肥又快,田里的稻子,金黄灿灿,穗子饱满,累累实长。父亲说,要准备“双抢”了。
母亲一早买了几斤肉,还打了十斤谷烧酒回来,准备“双抢”犒劳。父亲请王木匠来家里修脚踩的人力打稻机,并同王木匠一起回忆旧社会的产量和农具。父亲说:以前亩产三四百斤就是高产了,用一个扮桶,一亩田要扮两三天。现在好啊,有政府的优良种子,有农药,碳铵,尿素,又种双季稻,早稻亩产都有五六百斤,晚稻搞得好都七八百斤。最进步的是有打稻机了,人员调配好,不包括杀禾,一天收三四亩田的稻子都不是梦想。
夕阳下,闷热比中午的火热更令人窒息难受。太阳一下山,我和父亲早早来吃晚饭,父亲喝了点酒,也倒半杯给我,母亲用辣椒炒的五层楼肉格外的鲜香。我喝完半杯酒,双眼盯着父亲,意思还想筛点酒喝。父亲明白,也知道我酒量,便又倒了三分之一杯烧酒在我杯里,说等下去塘坳生资部排队抢买化肥,千万不要与别人发生口角和打架。我点了点头。我感到很开心,十五岁的我可以帮父亲挑粪担水,背一百斤包的尿素不用别人起肩,我终于可以帮父亲替手了,可以更进一步减轻父母的辛苦与劳累。这是我“三岁牯牛十八汉”,长大了的意义和成长了的价值。
2
“双抢”是一场战役,在时令季节里,抢收还得抢种。抢收需要什么,抢种又需要什么?父亲像临战的将军,把战前战后都要安排好,并要清楚每一个细节。
木达柜里还有不少粮食,父亲常常从田里回来反复计算,今年除了上缴国家,可能会有两千多斤的粮食剩余。这是从小吃不饱饭的父亲心里感到最幸福的事,一种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勤劳致富的富足感,像清风吹拂父亲的脸庞。
父亲下了一个决定:“双抢”之前必须建好一个由红砖和水泥预制板做成可放下一两千斤谷子的达柜。我和父亲都没学过泥水匠的活,但却有信心来砌好这个红砖达柜。父亲不知从哪里借来泥水匠的砌刀、沙板和荡子,一早上,就把红砖和从踏水桥下捞来的沙子与鹅卵石挑到楼上,又买来两包双丰牌水泥和一些六毛丝(六厘钢筋)。父亲先计算好达柜的盖面面积,然后倒制盖板水泥板面。父亲说,水泥板倒制好要三天才可以起动拿起来,所以要先做好。
由于不是专业泥匠,又要做准备工作,第一天,我和父亲才制好几块达柜的水泥板。第二天,才从母亲那里拿些补衣的线,开始开线砌达柜了。由于考虑承重,父亲砌六厘米宽的砖墙,我做小工,也是到天黑才砌好砖体。第三天,才把砌好的砖体内外粉刷好,用水泥油光面,待抬水泥盖板盖在上面,漂亮结实容量很大的红砖蓄粮达柜建成了。我望着父亲,父亲望着我,开心地笑了。那晚上,我和父亲每个人又喝了一杯烧酒。
3
煤油灯昏暗,火与焰直拉拉的,打开的门窗,没有一点风进来。
父亲和我们每人一把蒲扇不停在扇。好热,又好多蚊子。
父亲坐在堂屋的角落里,没有过滤嘴的五岭牌香烟在口边闪闪发光又嗤嗤作响。我感觉到,父亲临到“双抢”时节,和香烟一样在燃烧,包括他的生命和激情。
“人都请好了,请的人明天有一桌。吃饭时,我们自己家的不要先上桌,让他们坐桌子。另外,明天中午吃点心,糄粑就不要上了,多些绿豆稀饭,多买些西瓜香瓜。”父亲在安排第二天的战事:“炎天水热,菜清淡点,难恰水。”
“那汽水买不?”我问父亲,我最喜欢汽水。
“汽水一毛五一瓶,划不来。”父亲的话就是指令,我有点失望。
“担谷的箩筐子准备好了没?”母亲提醒,“箩箕索和扁担还没换新的。”
“这些准备好了,明天哪个踩打稻机,哪个出桶,哪个担谷,哪个杀禾,哪个抱禾垛子,哪个合管(稻草收完谷合成捆便于担回家作柴火用),我都心里有数。只要天不下雨,明天这个刀把丘三亩五分田搞完没问题。如果打稻机不出问题,下午那些稻草都可以担回来。”
父亲确实如位田耕将军,我打心里佩服。那时我想:我长大了,也要学父亲一样,做一个像样子的有担当有风骨很坚韧的农民。
4
从由轻到重的呼唤声中醒来,我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下了床。走到禾堂坪,天刚蒙蒙亮,启明星还在东方一闪一闪。南岳山上有了鱼肚皮,我生活的地方,太阳一直就是从那山顶上升起的。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隐约听到远处的垄里传来了踩打稻机的响声。原来,还有比我家更早的人,已经在田里干起来了。
三伏天里,清晨还是感觉到清爽。风,从南边吹来,吹动着母亲要我去剪、我就是不肯去剪的长头发。
我挑着叠起来的两担箩筐,箩筐里放着用酒瓶子装满的打稻机齿轮润滑的粘稠黑色机油。父亲告诉我:先把一些东西放到田边,然后回来背打稻机的滚子。
打稻机的滚子是由两个圆形铸铁、一根长轴和轴承以及多块杂木组成,每块木上有序地装有铁丝 成的打稻指,不好背,扎背心痛。
痛得不行了,我便在垄中间小河的桥上放下来休息。抬头望见大姑父朝我家的刀把丘走来。
姑父是退伍军人,办事雷厉风行。父亲托人附信要姑父今天来帮忙,没想到,天刚亮,姑父就来了。他没进屋,直接赶往我家田里。父亲包了别人的田,我家要耕种的田比别人家多很多,姑父经常来帮父亲,所以我家田土在哪里,连哪丘田稻子先熟透,大姑父都知道。
大姑父帮我把打稻机轮子背到田边,我发现田里已经有几个人弯腰在田里割禾。
太阳露半个红圆球,霞光照着他们的背影。尽管早上清爽凉快一点,但那是相对中午。农历六月,三伏天里。就算是大清早,我也看到他们脖子上搭着汗巾,不时地用汗巾擦去脸上和眼角的汗水。
待我拿着镰刀走过去割禾时,发现他们是生产队的堂叔堂婶,还有不会犁田、来我家换工的叔婶们。
“早起三早当一工”,我看到隔壁生产队也有很多人迎着朝阳在收割早稻了。
5
当父亲和大姑父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还试踩了打稻机,听声音纯不纯。这时,弟弟来田边喊大家吃早饭了。我发现,我家这丘田,割禾割了快一半了。一垛垛有顺有序地摆放在田里。
回到屋里,一桌菜已做好了,个别菜已经凉了。结果一桌坐不了,多来了三个人。大姑父一边给自己倒酒,一边说:“多拿几个丁椅来,坐挤一点。”于是我也挨着桌子角坐着。堂叔喝一口酒,对坐在一边的父亲说:“老兄的田,作得好,禾头好沉,产量要超过别人。”
父亲在一边暗自乐,想回话,却让母亲接言道:“作什么好,你们家的禾也长得一样好啊。”
大姑父直接夸父亲:“我屋老兄,是农民状元。”
我端着碗,瞟过去看父亲,父亲正在用筷子夹一块肉往口里送,脸上露出和朝阳一样的笑容,也像是小孩被大人夸了一样的开心。
早饭吃完,赶天凉快,大家带好开水、斗笠、草帽,一路像支队伍往田里赶去。时已是八九点钟,太阳开始发热烫人,偶尔一阵南风吹来,让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只不过南风并不是想来就有。农村的“双抢”,就是在一年最热的时候进行。
6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中午吃完用凉井水浸泡过的西瓜香瓜和点心的时候,就快收完三分之二了,估计中饭后不用多久就可以收完。这时,大姑父问父亲:“老兄,是不是二十一个毛挑子了?”一个毛挑子是指一担刚从打稻机里出来没有筛干净、伴有禾衣子的谷。
父亲擦了擦脸上的汗,掏出五岭牌香烟,给抽烟的叔叔们散了一轮,一边用汗浸透的火柴划火,一边笑眯眯地说:“嗯,这挑子不重,少打了一次药水,少下了点钾肥,谷粒不壮,不扎实。”堂叔接话:“老兄人不知足,挑子咯重还嫌不扎实。我挑了几担,肩都压肿,要是我屋扮禾,挑子有咯重,我买‘回雁峰’给老兄喝!”
扮禾,是最有乡情味的一个方言词语。“小暑小扮,大暑大扮”,这是句老帮人的话。意思是,小暑节气里,那些早熟品种已有部分可以收割,大暑节气里,所有的早稻都可以收割了。以前用的是扮桶,用个篾围子围住个长方形立体木桶,用双手抓紧一垛禾,用力猛洒让谷粒在篾围子里脱落,和洒麦子脱粒一样,千百年来都是这样。人辛苦,效率低,而现在用的是新型农机设备,比以前不知快了多少倍。父亲常常知足自豪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遇上了分田到户,遇上了只要人勤劳下狠,就不会穷也不会饿的好时代!
天气还好,南风稍多,中饭后没休息,三点半的时候就收完了三亩五分田稻子。父亲像打了胜仗似的,感谢各位叔婶亲邻,并让他们早点回家休息,然后,还请他们晚上来我家吃晚饭,打算留下姑父与我们一家人用竹杠子来挑捆好的稻管回去晒干,用作以后生活柴火。叔婶们却一个个不愿回去,一起帮着我们挑稻草回去,还有的帮母亲在晒谷场上筛谷。
7
夕阳下,火烧云,天色渐晚,热浪渐退,清风徐徐,炊烟升起。
晒谷场上热闹起来了。几户今天开始扮禾的人家用竹子做成的三把叉下,吊着个竹筛子在筛谷,也有人用木仙子(手摇的风车,用来吹瘪谷的)在吹已经筛好的谷子,禾衣飞扬而去,壮谷落在箩里,尾子做火料或放鱼塘作鱼草,二瘪稻用袋子装好准备磨粉喂猪,壮谷晒干后先送国家粮站,多余的存起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丰收的盛夏傍晚,忙得不亦乐乎。
晚饭后,晒谷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轮明月,跟着太阳的轨迹,也是在东边的南岳山上升起,照耀着大地上还在忙碌的人们。打稻机的声音还隐隐约约听得到,和清晨一样,不知道是谁家那么下狠,出月光了还没收工。我估计他们家应该没有和人家换工,也没请到帮忙的人,又想抢时间收完那田里的谷子。
晒谷场上,全生产队和我年纪差不多或少一些的人在开心地游戏。月光下,有的用粉笔在沙黄泥光面的晒谷场上画个图形,用田螺壳串起来,用单只脚在踢动田螺壳,叫“踢房子”。也有人在做“卖狗卖狗姐姐,卖给河边奶奶”的游戏。我现在都不知道,“铜老板,铁老板,买狗呗”,那是什么意思?
萤火虫出现了,像满天繁星散布在眼前和田间稻禾上面,一只只像打着一个个微型的灯笼在赶路,匆匆忙忙,突上突下,一闪一闪。
有人在晒谷场讲故事,周围坐一堆拿着棕叶扇或纸扇的人,一边打蚊子,一边听得津津有味;有人在捉萤火虫。还有几个小姑娘在一片青蛙和虫子的叫声中,坐在晒谷场的南边,望着天上的月亮,在唱那首我从小就耳熟能详但一直不知其来历不知其意的童谣:
“萤火虫,耀耀光。借我锁匙开我箱。偷我牛,犁大丘,偷我马,到衡州。衡州路上有口塘,打甲鲤鱼八尺长。娘吃尾,爷吃脑,留答中干讨嫂嫂。嫂嫂你莫哭,三间瓦房是你屋。三筒白米要你达,达成粉,做成粑。打成鞋底绣成花……”
当很多人都回家后,晒谷场多了几张竹凉床,上面用三把叉和木谷耙支起的蚊帐。在皎皎白色月光之下,它们如同几个小小的营帐。母亲在家里洗一堆碗,洗一家人又泥又汗的衣服,父亲在月光下的垄里给田里灌水,准备明天早上开始犁田。我在晒谷场和另外几户人家的人在守各自的谷子。收音机在竹床底下传出张海迪轻轻的悠扬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8
也许武侠书籍看多了,我好像在梦里,梦里跟一位须发已白的老人在学绝世武功。梦里的我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佩一柄长剑,准备闯荡江湖,独步天涯……
突然感觉鼻子不能呼吸,一下子从梦中憋醒。原来是有人捏住了我的鼻子。我定神一看,是来帮我们家帮忙的老表。老表笑着对又黑又瘦的我说:“黑皮,在做什么美梦呢?”我一下子从晒谷场上的竹床上坐起,看到东方天边太阳又快出来了。
父亲也来了,拿两把锄头给我,要我们去刨田埂上的草,并锄好田型,做好田间防漏水。
田里的水有脚踝那么深,一阵阵清凉从脚板涌向全身,田埂上的水草,尤其是吊牛草十分茂盛。用锄头刨去草,发现了田埂上有不少鼠洞和被黄鳝钻的洞。该死的还有一种村人叫“土狗子”的虫,也把田埂钻得千疮百孔。如果不处理好,撒在田里的肥料便要流失到别人家的田里去。所以,锄田型在犁田之前是必修课程。
我幼小便跟随父亲在田里土里摸爬滚打,除了用牛犁田不会,其他方面那是样样皆能。九点饭后,我把肥料担到田边。父亲已经把牛已经牵到田里装上了犁,在田里一声声骂牛唤牛,一圈圈地犁起来了。
“滑——”父亲突然一声把牛叫停,牛扬起头看天边。我回头看父亲,父亲用手示意我过去,意思让我去学。我兴奋得很。父亲在水田里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许多细枝末节。父亲说,驾牛犁田看起来是粗活,但也开不得小差的。他讲了很久,待我接过父亲手里的犁跟在牛屁股后面,我学着父亲的口腔,对牛一声吼过去:“特气(赶牛走的口音)——”牛就迈开了脚步,拖着犁铧,还回过头,不把我看在眼里。
走一两圈,我扶犁不稳重,一下轻,一下重,犁河便一段浅一段深。那牛有点欺负我,突然一阵狂奔,把我拖在田里。父亲一看我还不行,把我从田里扶起,老表指着满身泥水的我,捧腹大笑。父亲让我回家换衣,便又自己犁起来。父亲说,田犁不好,禾长得也会不好。我感觉得到,父亲盼望我快点长大,好帮他替手。父亲从小就是一家的顶梁柱,一直没有人替他分担忧愁。我感觉到父亲在炎天水热里的辛苦,只是父亲硬着骨头不表露出来,坚强得像个铁人。
9
又是一个晨曦。
人们陆陆续续走向田野。有的去割禾,有的去扯秧。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田里气氛热闹起来了。那些怕晒黑的姑娘和新媳妇以及新上门的姑爷,戴斗笠还用脸帕把脸挡住,长长的袖筒子把双手包扎得严实,太阳无论从哪个角度射来,都晒不到他们的皮肤。为了白和美,他们裤子裤脚不卷起来,直接走在田里,好在一届“双抢”后,他们脚不变黑。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又加上天气太热了,我开始有些吃不消。看到别人家田少,几天就差不多搞完一大半,还有一些人家里女儿在处对象,有准新姑爷上门一做就是半个月。而我家,就是一家四人硬顶,虽然我家请了不少人工,除了亲戚家,那大多数是要还工的。我一方面开始嫌父亲不当包这么多田来种,但另一方面看到父亲母亲没日没夜劳作,不敢表露不满的心情。我多么希望天气能凉快一点,不要那么热。
太阳如火,烈日当头,赤脚的脚板,将田埂上的荒草直踩在脚下且入土三分。编织箩里的谷子干干净净,并没有多少禾衣掺杂在里面。我看到挑谷的堂伯伯上身赤裸,古铜黑悠的皮肤在阳光下闪亮。六月落雨隔座墙,而且还没定数,豆大的雨粒来势凶猛,但当人们赶到晒谷场收好谷的时候,它又忍不住下了。雨粒打在堂伯伯身上,像打在荷叶上一样,那皮肤上黑色素超标,已不粘水,也有些油。雨落在他身上,瞬间滑落而去。一阵雨后,看不到他上身有湿的痕迹,只是他的裤子,那是没下雨的时候,早已经被汗水浸湿透。
扁担比手板宽多了,但也压得弯弯的,让我担心扁担随时会“咔嚓”一声断了。堂伯伯一步一个脚印,脚趾扣到泥里,一步三滑,肩膀上的担子却平平稳稳。
晚上在床板上睡不着觉,望着窗外的星星,一阵阵风吹进来,我听到远处的虫子叫声。
10
那天上午,我埋头在插秧,突然有人来报信说:“军佗,你屋爸犁田出事了,你过去把你爸背回家去吧。”
三十九度的气温,田里的水烫脚,听了报信的人的话,我背后一阵阵冰凉。赶到父亲面前,我眼泪止不住滴答往下流。
父亲坐在田埂上,田埂上一摊血,田里的水掺和着父亲的血,在太阳下暗黑沉沉。父亲看着我,一脸的困苦,他的意思是,家里还有这么多事,还有很多换工没还给人家,自己却在田里让玻璃撕开了脚板,这阵子没法干活了。除了无奈,父亲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有一种自责感。
没有风,热如炽。牛站在田里不动,用尾巴赶着牛蚊。犁,歪在田里。田里的犁河水中,有泥鳅,水虫在里面匆忙地游荡。
时间,在我望着父亲的眼里凝住,我感觉到,田里的玻璃也撕开了我的脚板,虽然没有血,我却也是抽心地痛。
我家的“双抢”像一场持久战,才进入中后期。别人家里田少的圆了秧田门。当时的口号是“插完晚稻过八一”。我们家垄里的大块田都已收种,剩下山坡下的排田了,排田面积少,一条一条狭长。父亲受伤不能用牛了,我们便想要用锄头挖田,然后用耙头梳烂田泥,用楼梯拖平田泥,再插秧。
排田不是用堰头的水来灌溉,是要用水库的渠道水来灌溉。生产队渠水引放由父亲和两个叔伯承包了。父亲白天在田里收种,晚上还得去引渠水放进生产队的塘里,以供排田灌用。父亲的脚受伤了,晚上就是由我代替父亲跟一起承包引渠道水的伯叔们,打着三筒电池的电筒,沿着渠道埂子在荒山野岭里走上几公里路,从水库主渠中的水闸口,一路堵上分水口,直把水引到生产队的池塘里。有时候累了,我们就坐在坟地边的水泥地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一边打蚊子,一边盼望水快点流进塘里,然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当天亮我醒来回家的时候,我看到父亲一拐一拐在离家近的排田里赶着牛在平田的背景。我眼前浮现父亲脚板上两寸多长可以看到骨头的伤口,才一两天,伤口根本没有愈合,那伤口里面肯定又挤满了田泥。父亲脚下的伤口,当时就像在长我的心上,里面也挤满了助长发炎的田间泥水,让我感到一阵阵生痛。
11
一眼望去,炽热的阳光下,垄里的禾已收割,终于只剩下一点点没收完了。“双抢”,是人与牛的体力透支和汗水流虚身体的无怨无悔。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家包了别人家的田耕种,所以,谷子多,家里红砖达柜也无法堆放,“双抢”没搞完,便要把一些谷送到国家的粮站。
在粮站,谷粒在晒谷场筛了又筛,用木风车吹尽不饱满的谷粒,还晒得谷粒要裂。来到粮站,不少人还是提心吊胆,怕谷不过关。粮站验谷人员,脸上露出神圣不可亵渎的庄严。
轮到我家,谷是晒干透了的,验谷员没说啥,只做了个可以了的手势,意思去过秤吧。父亲和我的脸上露出实诚和胜利的笑容。父亲说,给国家送粮谷,一定要送最好的,一定要晒干。所以,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每一次来送谷,提心吊胆之后,基本上都顺利过关。
粮站的斗秤,在二楼。我和脚上有伤的父亲把谷一袋一袋挨家挨户排队搬到秤前,倒到秤斗里。秤到第五秤时,那管秤的和记账会计质问我父亲:“你家多少田?有这么多谷卖?”父亲说:“连自己和承包别人的田,有十一亩。”秤员与会计说:“你送来的谷,超过了粮折子上的数目,我们不能收。”
父亲像触了电,一下子蒙了:这下如何是好?
我走上前对他们说:“我家的谷又干又壮粒,为什么不收?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没有别的地方卖,你们为什么不收?”
两人看着又黑又瘦但精气正充沛的我,说:“粮站放不下那么多,我们现在只按粮折子的价格和数量收。这是上面的政策。”
看到愣在那里的父亲,秤员和会计说:“这样吧,你去把谁家不用卖谷的粮折子和承包谁家的粮折子一起拿来,顶够这次的数,下次就不要再送来了。”
“双抢”这段时间,父亲带我们一家,还请了不少亲戚帮工,白天黑夜都没休息,而且受了重伤,还中暑发痧病得九死一生,收获了不少谷子。而此时此刻粮站的人不收,我看到了父亲的无奈和心寒。那一刻,我同感着父亲的难受,暗暗下决心:以后读不出书的话,也一定学门手艺。小小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这辈种田人的各种辛酸和苦难。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苦笑看着我,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来:“明年我们家改种一些经济作物,种西瓜,种芋子,种荸荠……”